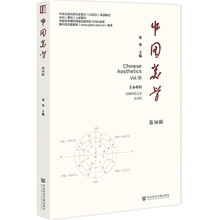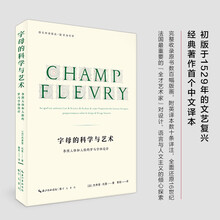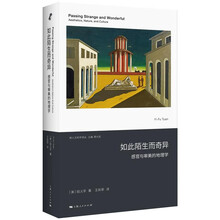这个例子反映出传统《诗经》注释的必要性与弱点。这首诗需要被整合在一起。注释者通过狼的窘境引发人思考(“兴”),同时缩小“公孙”之义,锻制了狼主题与公孙主题之间的联系。陈奂所发现的偶然矛盾正是《毛传》的注释风格。但周公故事与这首诗的关联——这种关联对注释者来说当然是既定的,肯定下来却没有用相反的注释验证过——对说明诗歌第一节中“公孙”的形象怎样有助于赞美成王的叔父周公很重要,而《毛传》就将“公孙”解释为成王。高本汉(Betnhard Karlgren)将这一点简化处理,注释这首诗为:“一个年青贵族被比喻为一只凶猛跳起的狼。”①这可能就是像高本汉这样从文本内在出发的读者从传统学问中所能“拯救”到的一切(而“拯救”正是合适的词:没有背景的读者也许看到这只皮肉下垂的狼不是凶猛,而是滑稽)。②现在肯定的是:注释者将诗与周公联系在一起,超出了《狼跋》一诗自身在文本上所具有的任何可能的意义;如果这种联系是可疑的,那么注释者倾向于将《国风》中所有诗都解读为周代君主政治教化的证明(以及成果),注释者的以上假定与这种倾向相吻合的方法只会使诗歌与周公的联系更加确定。这也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诗经》解释学派的特征之一:《狼跋》注释的意义依赖对此诗前面五首诗的注释,那些诗转而不断指涉另外一部经典《尚书》。③古老的《诗经》中的一切都是交互指涉与互相确证的。现代读者不把这部经典看作周代的编年史,而是把它看成(再次?)毫无联系诗歌组成的总集,但数世纪以来,它从来不是这样的总集。
希波吕忒:那该是靠你的想象,而不是靠他们的想象。
忒修斯:要是他们在我们的想象里并不比在他们自己的想象里更坏,那么他们也可以算得上好人了。两个高贵的动物登场,一个是人,一个是狮子。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六幕
简言之,比较幸运的是,过去几年关于“中国讽寓”的争论对它真实性的关注不如对它可能性的关注那么多。甚至那些乐意给讽寓在中国文学中安一席之地的学者对这个术语也持保留意见——而这些保留意见被别的批评者拿来当作全面摈弃中国讽寓的理由。可见问题纷繁复杂的程度,它使得在别的方面观点都相异的批评家,如宇文所安、浦安迪及余宝琳对中国文学世界的结构几乎持相同的见解。
在探讨中国18世纪长篇小说《红楼梦》时,浦安迪观察到,对于《红楼梦》所有的“另一层意思”的轮廓描述而言,它“只是没有让自己符合讽寓性阅读,而20世纪的中古研究者一直引导我们用这种类型的阅读”①。余宝琳更强烈地反对(中国有讽寓的观点):对她而言,中国与西方的个案不能看作是单一的、定义非常宽泛的“讽寓”的变体。中国的模式,“尽管表面上(与西方的)相似,但建立在一套与西方的隐喻或讽寓根本不同的前提之上”(页116)。
能区别欧洲讽寓与会被误作讽寓的中国类似物的特质是什么?我们经常会错误地将两者混淆。对所有批评家而言,标准的表述是:讽寓“言此意彼”,它是一种“持续性的隐喻”。①余宝琳对后一种表述特别心有戚戚焉:出现在讽寓中的东西必先出现在隐喻中。至于后者:
由西方隐喻设置及沟通的、最根本的分歧并不仅是言辞上的——它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本体论范畴内,一个具体而另一个抽象,一个可感而另一个不可感知(页17)。
西方本体论与文学理论(依余宝琳所见,他们一直在西方传统中运用)的关联是完整的。讽寓“创造了有两个层面、等级式的文学世界,每个层面都保持着自己的连续性,但只有一个层面拥有终极的主导地位”(页19)②。隐喻与讽寓两者都体现了一种无所不在的规律,即模仿或虚构的规则:
模仿……基于一种根本的、本体论的二元性——这种假设认为:有一种更真确的现实性超越了我们所处的具体的历史领域,而两者的关系在创造性活动与人工制品中得到复现(页5)。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