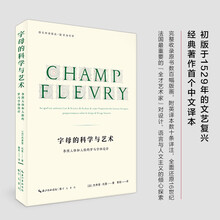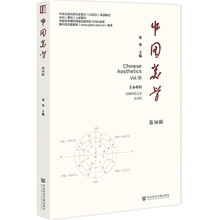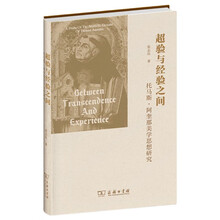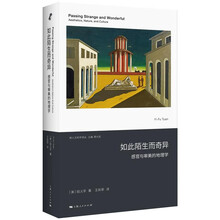启蒙现代性所表现的自我反思与文化批判,早在明代中期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失落的文艺复兴”时期与清代社会、学术思想发展的几个时期,针对政治制度的腐朽、文化的颓唐、国运的衰落,已经发动起来,流行开来。随后针对封建王朝体制所引发的各种弊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作的犀利的揭发与批判和所发动的改良主义运动,达到了启蒙思想发展的高潮,也可以说是启蒙现代性的高度体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流亡中进行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体验了迎面扑来的西方世界各种新思潮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新经验的思想激荡,接受了了日本的各种来自西方的启蒙学说,如民权、自由、司法等,并宣传“破坏主义”。他说:“历视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在谈及卢梭的《民约论》时,当时梁启超情绪激昂,想象着卢梭的民约思想一旦传到东方,老大中国就能变成自由乐土,因而用诗一般的语言祷告:“大旗觥觥,大鼓咚咚;大潮汹涌,大风莲蓬……《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与此同时,梁启超大体上接受了日本的启蒙家中村正直的“新民”学说,而促使其思想为之一变。中村正直师法西方,认为西方列国的强盛,在于人民具有优良的国民素质,他与其同时期的日本启蒙学者一样,认为维新的真正意义在于“人民之一新”,而不是“政体之一新”。梁启超在(自助论)(1899)一文中介绍了这位日本大儒的学说,并在其影响下提出了要从道德教育人手,来改造国民的性质。正是这一目的,引起了梁启超对我国“国民性”的探讨,转入对“新民说”的呼吁。<br> 19世纪末,国民性的反思,以严复、梁启超等人为发端,成为我国社会启蒙思想现代性发展中的一个极其深刻的论题。国民性不同于民族性,它是正在进入现代社会的我国国人,在近代封建极权社会、政治、文化高压影响下形成的相当普遍的习性,奴隶性是其最为突出之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