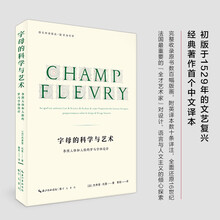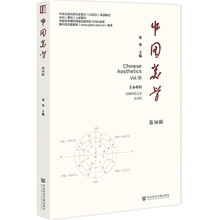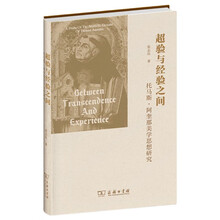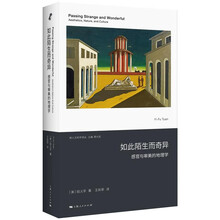上篇 晚明士人的个体生命情怀及其哲学意蕴
第一章 感伤:唯我之暂存的困惑
晚明士人的伤逝情怀是个体生命对文化的承载与重构。中国文化对个体生命精神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缺失。儒家“克己复礼”,将小我的生命放置于人群社会中体现价值,宋明理学更是施以“存天理,灭人欲”的高压。晚明士人对生死问题的探讨恰是源自驱力与文化限制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痛苦感。这里的驱力是指晚明士人内心渴求的人性自由。这种自由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机能。“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洒脱,本无挂碍系缚”①,“人心虚明湛然……惟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它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②,认为心是自由的,无拘无束,可上天入地。其二,是人的生理内驱力。“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③,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好货好色”④是人的本性,肯定男女间热烈的感情,极力讴歌世俗生活的享乐。尽管心取消了“为善为恶”的防检,解除了“闻学”“守礼”的桎梏,也抛弃了世俗之见的干扰,然而晚明士人的放诞任真只能勉强摆脱自身内在的拘泥,却无法解除外在的束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