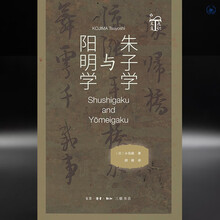自正德五年至正德十年的六年,是阳明一生中职事变化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然所居大抵为闲职,并无繁忙的公务,因此它实际上便亦成为阳明较能集中精力讲学的一个时期。从北京到南京,凡所之皆无非讲学之地,因此其门徒益众,而学术影响亦日增。就阳明思想的发展而言,这六年是他将龙场之悟进一步扩充、完善,并使之体系化的重要时期,亦是其学说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实际形成的重要时期。他将关于心体的学说以及知行合一的学说贯穿于儒家原始经典的系统诠释之中,超越朱熹之学的固有规模,而单独开辟了一片广袤的天空。与徐成之论朱陆之学,实际上即已然公开表明其思想之逸出朱学藩篱;而在越中与徐爱论《大学》之旨,其主要内容即今《传习录上》的前半部分,则是阳明对朱熹格物说进行比较系统的公开批评以及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开始形成的基本标志。其学说在当时学术界所产生的思想震动,从徐爱的记述则亦约略可见一斑:“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始而“骇愕不定”,终而笃信不疑。徐爱的这种反应,在当时闻阳明之说的学者当中或许是普遍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