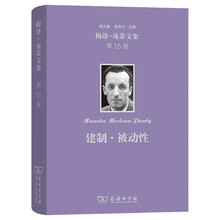这种差异性,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康德在他对认识客体的认识论反思的文章中坚持认为没有对物自体的理智直观,这是正确的。但是儒家坚持认为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寻找对终极目的的理解,也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也是正确的。在这里,就像性和理那样,命正好是物自体,这一点在宋明新儒学的庞大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详尽说明。
在此,挑战性的问题是:“穷”和“尽”和“至”是否能大致被解释为一种理智直观。牟宗三通过热忱的努力来反驳康德以表明:儒家有关于物自体的理智直观,因此儒学把人放到在西方神学和形而上学传统中上帝的这个位置上。这是因为牟宗三把人的心灵设想为好比上帝似的无限心灵。但这是一个在错误框架中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一个上帝所拥有的那种假想的无限心灵,但是我们的物理界限并不能阻挡我们拥有关于实体的持续的自我超越的经验,这种经验并不受有限心灵的限制。心灵确实有关于无限的视野,并且能不受限制地把它用于从事自我超越的创造性过程。这是一种不同的设想人类心灵的方式,这种方式表明在人类起源、人类意向性和人类行为上有限性和无限创造性的统一,这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和本体解释学的思考框架。
从本体诠释学来说,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框架的转换和重新解释的宇宙本体论范例更恰当。但是牟宗三确实有这种解释学的或本体诠释学的意识,并且做出了注定是要引发不必要的但却是很热烈的争论的论断,这种争论遣责它误解了被海德格尔和其他西方形而上学家所经验的人的形象——一个有限的存在者——并与其相矛盾。根据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对作为物自体的终极的概念不必是某种直观经验,而是基于对被我称为超融的反思的结果。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一个人能发展和体现一种观念和感觉的自我包容感,这将会证明我们对价值的信仰并且引导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看待理智直观,那么,我们也许看到我们能制作和拥有理智直观,它不需要客体的概念化而只是需要态度和心理的形式,它能在一个创造性变化和精神的发展的开放世界中丰富个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没有那种必须指向超验客体的理智直观,即使我们可以避免概念公式上的矛盾,或者把它和关于实体的科学知识联系起来。这是两种需要分开讨论的论题,但是,可以被认为与人类存在——作为在发展中的动态的整体经验——的序列联系在一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