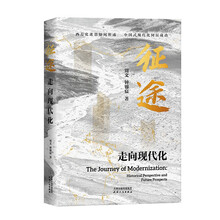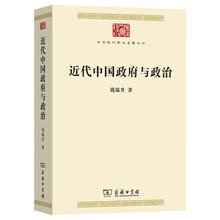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一个被疝气病和头晕病折磨已久的老人离开昆明,踏上了东归故乡之路。此人就是刚刚卸任云贵总督、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的林则徐。岁在己酉的1849年,林则徐六十五岁,在官场驰驱了大半辈子的他已是力疲心瘁。尤其是近十年来,从遣戍新疆伊犁,到重新起用后驻节于多事的陕甘、云贵,衰惫之躯已越来越让他有力不从心之感。
去北京,还是回老家福州?动身前,林则徐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任职北京的女婿沈葆桢竭力促成退休的老丈人进京居住。林则徐早先亦有此意,曾委托京中老友代为觅屋,但京城官场繁重的应酬让他一想起来脑袋就发怵。不出门吧,恐怕引起招怪;出去应酬吧,又与告病名实不符,万一哪个小人背后射来一箭,尤为不值。更让他担心的还是北京寒冷的冬天。这几年一直在南方过冬,从来不用穿什么大毛衣服,万一不适应京城如许寒冷的气候,旧疾转重,那真要把一把老骨头扔在皇城根下了。
但是,故乡福州也并非宁静的乐土。二十年不履故土,林则徐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文藻山背后倾坍的老屋和庭院里疯长的荒草。几亩薄田,外加几间东倒西歪屋,使他归来事农圃的田园生活设想也会在事实上成为一个泡影。从云南昆明刚启程至曲靖,在写给女婿沈葆桢的一封信中,他对自己能否在故乡长住表示出忧虑。这一忧虑随着家乡的逼近越来越困扰着他。扶病东归至南昌,林则徐在百花洲淹留了四十余天。固然是旅途过于劳顿,他要觅医诊治,但在一封写给朋友 卧榻之侧何人,让林则徐一提起来就耿耿于怀? 他的故乡福州城,已在1844年的夏天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向西方世界开放。1845年1月,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争得他的领事馆人员入住福州城内乌山积翠寺。从家乡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此事时,林则徐已在署理陕甘总督任上,此事曾引起他的忧虑与警觉。一个宦游在外的人,怎忍心看着故乡成为一个“腥臊之窟”?那时他就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慨叹:“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焉,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五六年来,东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彼时距1840年的那场中英之战才过去四五个年头,作为这一改变近代中国进程的事件的主角之一,林则徐已经深感历史的吊诡了。
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下旬动身,至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林则徐终于抵达想回又不忍回的故乡福州。从昆明到福州,这一程路他走了近半年。姑且不论交通的不便和身体上的原因,他实在是走得过于慢了一些。
自道光十年(1830)离开福州,二十年过去了。文藻山的房屋久未修葺,也少人打理,再加临着穿城而过的闽江的一条支流,地势低洼,汛期发大水时留在梁柱上的水线还宛然可辨。欲行另购房屋,却又力不从心,他多年行走官场,但没攒下什么钱。林则徐把住宅第三井的双层楼房稍作收拾,就住了进去,这就是后人俗称的“七十二峰楼”,楼上是他的藏书室兼工作室“云左山房”。
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现在有时间去回忆自己并不宁静的一生了。从京城的翰林院,到武昌,到广州,再至遣戍西北,这就是他的官场之路。人生就像一个白痴画的并不太圆的圈,他现在又回到了度过整个少年时代的这座多雨的南方城市。他读书,写作,整理宦居各地时写下的诗篇,日子过得看上去似乎波澜不惊,但病痛袭来时遮天蔽日的黑暗却时时挑战着他的意志力。有时,他不无悲观地觉得真的熬不下去了。这一时期往来信件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被病痛折磨的老人形象:
1850年,驻节福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帝国的著名能吏徐继畲。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由福建布政使升任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接到道光皇帝的命令,返回福建出任福建巡抚并兼办通商事务。道成年间的帝国政坛,这般朝令夕改的事情并不只是落在徐继畲一人身上。按帝国官制,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都驻节福州城,但这一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由徐继畲代理总督职务,他成了福州城甚至闽、浙两省事实上的一把手。
现在,他的官帽上沿缀着一颗红珊瑚,官服的前胸后背都绣着锦雉。作为全国十五名巡抚之一,他的级别是从二品,上司的缺席使他兼署闽浙总督一职,同时他还兼任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等职,以便更好地做好节制军务、考核群吏、监督乡试、代表朝廷管理地方上的财政税收,以及时人视之为畏途的办理通商事务等工作。
这个学者型的官员1795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有着浓郁书香的缙绅之家。在帝国官场上,徐继畲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应该算得上是根正苗红:在博学的父亲的指导下,还是幼年的他就开始接受儒家经典训练,尽管十九岁中举后,伴着青春期的闷骚他度过了十三年苦闷的时光,但1826年的会试及第,及后来朝考中名列第一的辉煌经历,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科场的宠儿。经皇帝召见,他荣幸地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国家的最高学府继续他的学业,并在不久后晋升为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