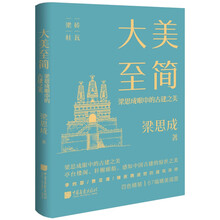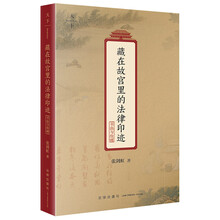1979年秋,我突然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今天》,是创刊号。“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最初,它很秘密地在我们《赤子心》诗社内部传阅。后来,那本珍贵的油印刊物,传到了宿舍。最后,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204寝室的12名同学一致决定,由一个人朗诵给大家听: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它是一根最细的针,同时它又是一磅最重的锤……那样的震撼,一生中只能出现一次。就这样,《今天》从我们的寝室传遍了77级,传遍了中文系。再后来,传到了东北师大。在此同时,它也传遍了中国各高等院校。
“北京东四14条76号刘念春”——对于三十年前《今天》读者,绝对是一组温暖的汉字抚爱。它们不再是地、名,而是一种新时代的灵魂慰藉剂。当年拿出三角钱邮寄一本油印杂志的穷学生们都知道,它的营养远远超过一碗红烧肉内部包含的全部味道。
忘不了整个1979年的下半年,我始终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度过。北岛、江河、方含、食指、齐云、舒婷……一个比一个更惊心动魄的名字,一次次击中了我。在最需要准确击打的时刻,《今天》恰巧加大了诗歌的投放——随着第3期、第8期“诗歌专刊”的连续推出,《今天》带着一种新鲜的美,带着一种时代力度,在全国诗歌爱好者的心中降下一场又一场诗的鹅毛大雪。
正是在一种近于痴迷的阅读沉醉中,我陆续用笔写下了我最原始的一些读后断想,并命名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诗歌评论。我把文章寄给了“刘念春”后,竟收到了北岛的回信。后来,它被发表在《今天》最后一期第9期上。在最后一段,我写道:“我敢假设: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一页上,我要写上几个大字——在20世纪70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它放射了奇异的光!”
幸运的是,在后来的年代里,更多的人和我产生了相似的感觉。而在一本本并不是由我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它们真的成了诗歌“主流”。
1980年夏天,我与王小妮在青春诗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今天》几乎全部主力。高瘦、清爽的北岛与芒克,各背着一个黄书包到《诗刊》售卖他们那已经更名为《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的伟大杂志。北岛带着我与王小妮绕来绕去进了一座灰暗的四合院。我记得小院子里围坐了二三十个文学青年。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孩,在朦胧的夜色中,用缓慢的声调朗诵了她写的小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