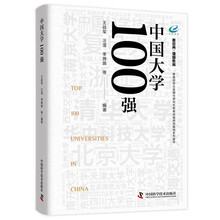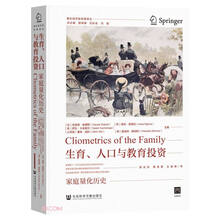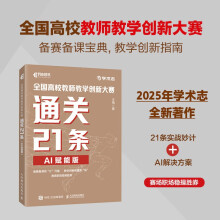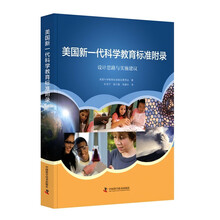他进而指出,国外同行非常佩服中国为教育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但国外对研究文章的评判标准与我们有所不同,他们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评论:一是方法论。国际教育研究界非常重视方法论,但中国的教育研究并不注重方法论。在上述65篇文章中只有定量研究文章明确说明其采用的方法。另一些积极收集数据的实证性文章往往未提及收集过程和他们进行推论的方法……这使人认为,在中国评价研究产出的是成品而不是过程……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研究往往是产生理论或修正理论。这样的理论可以丰富知识(即解释性的)或指出更好的实践(即指示性的)。知识的有效或实践的效果要得以体现,即使用不了几十年也要好几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只凭结论来评价研究产出呢?第二,各种社会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的复杂体……在国外学术界很难以固定的对与错作为支撑点,被所有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研究结论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们只能依靠其缜密的方法来评价一项研究,看其结论是不是通过大多数人认可的途径所取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评价一项教育研究的文章就像评价一篇数学论证一样。要替代评论研究成品的方法,你只得非常仔细地检查其过程……二是关于人的智力的依赖。对方法论的不重视和缺乏对研究过程的评价标准或许会导致国外研究者惊讶的第二点:信赖可以不依赖于数据的智力……数据、人的智力与数据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也是争论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好像不存在这类争论。相反,中国的研究者好像很一致,至少在理论上,在关于人的智力与外界之间的关系上是这样。毛泽东的《实践论》仍然是认识世界与客观的基础。换言之,大部分中国学者相信存在着客观实在,相信认识世界的‘感性认识一理性认识’的途径。因此,对人的智力的偏信不是反实证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反映。然而,对于人的智力的过于相信,认为‘思辨’的产品最具学术性,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文章仅仅是研究报告。国外研究者很难想象这种做法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