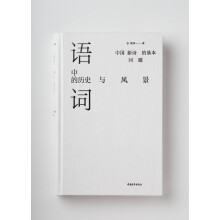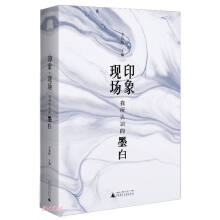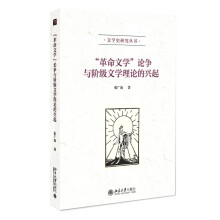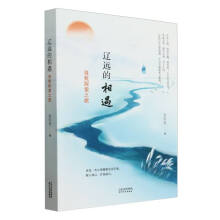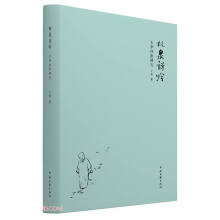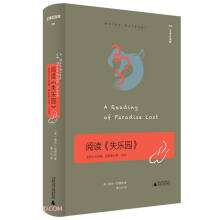如上所说,沈辽在薛向的推荐下任明州市舶司,应在熙宁四年三月七日以前,且才二年,由于明州市舶弃置,改监杭州军资库。但其太常寺奉礼郎一职并未被罢免。沈辽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祭祀其岳母彭城县君,作有《祭外姑彭城县君文》,其云:“维熙宁七年岁次甲寅,四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子婿、承奉郎、行太常奉礼郎沈某,谨以清酌庶羞,致祭于外姑彭城县君刘氏夫人之灵。……追往伤今,情何可任?辄陈薄奠,以抒余心。”表达了对岳母的哀悼伤痛之情。且可知沈辽于熙宁七年四月尚任太常寺奉礼郎。熙宁十年(1077)九月,沈辽作有《张司勋墓志铭》,悼念其岳丈张讽。文云:“以熙宁九年八月十日,以其官终于官舍,享年六十二。……女七人:太常寺奉礼郎沈某……其婿也。余尚幼也。公卒之明年,丧始自蜀归。诸孤将以九月某日葬公穹山先公尚书之兆,使来乞铭。”所谓“太常寺奉礼郎沈某”即指沈辽,此时他仍身任太常寺奉礼郎。《宋史·沈辽传》云:“久之,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转运使使摄华亭县。”亦可以证明,沈辽并未因明州市舶司之废,而不再任太常寺奉礼郎。
此后,沈辽又摄华亭县。《沈睿达墓志铭》云:“会秀州华亭阙令,承漕檄,摄邑事,而监司有挟旧怨者,因是搪摭万端,必欲危中以法。适民有忿争相牵告,事连及君,遂文致之。君不能与吏辩一切,引服受垢,夺官徙永州。”其被贬谪就是因为与人有旧怨,再加上“适民有忿争相牵告”,争论不止,以致得罪。据《挥麈后录》所云沈辽为人书裙带,由于被内侍得到,传到九禁,且由于近幸嫔御偶服之,被发现。“登科后,游京师,偶为人书裙带,词颇不典。流转鬻于相蓝,内侍买得之,达于九禁近幸,嫔御服之,遂尘乙览。时裕陵初嗣位,励精求治,一见不悦。会监察御史王子韶察访两浙,临遣之际,上谕之日:‘近日士大夫全无顾藉。有沈辽者,为倡优书淫冶之辞于裙带,遂达朕听,如此等人,岂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适睿达为吴县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时荆公当国,为申解之,上复伸前说,竟不能释疑,遂坐深文,削籍为民。”①明人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八九云:“辽登第后,游京师,偶为人书裙带,内侍买入禁中。神宗见不悦,会遣使察访两浙,就以谕之。时辽为吴县令,坐削籍。”②然此说似有可疑之处。首先,据《沈睿达墓志铭》、《宋史·沈辽传》等记载,沈辽不曾有过“登科”的记录;其次,沈辽不曾任吴县令;再次,沈辽虽尝摄华亭县令,亦尝任阳羡县令,但华亭县令、阳羡县令与吴县令并不同,且摄华亭县令的时间,并不在以上所说的“裕陵初嗣位,励精求治,一见不悦”之时,而担任阳羡县令的时间也不可考。而据第一章考证,王子韶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擢监察御史,而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上元县,时间在沈辽摄华亭县令之前,时间与之不合。③王子韶乃其二妹夫,用其它罪劾奏,似有欠妥之处,既与《沈睿达墓志铭》所言有不合,又与《宋史·沈辽传》云:“久之,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转运使使摄华亭县。他使者适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县民忿争相牵告,辞语连及,遂文致其罪。下狱引服,夺官流永州,遭父忧不得释”的说法有出人。若沈辽真有为倡优书裙带而受劾奏之事,那位监察御史也不应为王子韶,而是另一位监察御史。
以上借助《沈睿达墓志铭》、《宋史》、《宋会要辑稿》等资料考述了沈辽在此段时间的为官经历,而其它事迹亦可借助其诗文得以考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