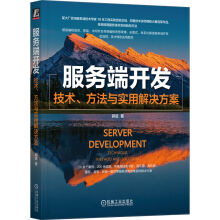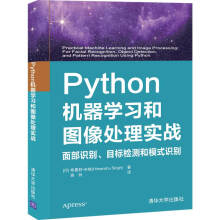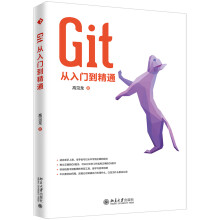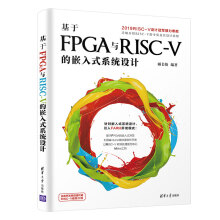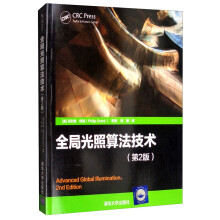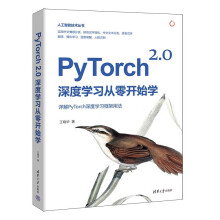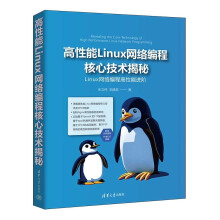以上情况意味着,说唱变文的场合,也就是进行俗讲的场合。它包括定期俗讲,例如春讲、秋讲;也包括各种斋会,例如三长斋日、八关斋会;此外还包括丧葬仪式。这可以在敦煌变文中找到内证,例如《目连变文》所包含的谈无常、语地狱、征昔因、核当果、谈怡乐、叙哀感等内容,恰好对应于《高僧传·唱导篇》所记八关斋会的俗讲内容。总之,尽管变文说唱也曾在戏场、宫廷、地方长官府宅和要路口演出,但是,其首要地点无疑是佛寺。
第二个问题是:敦煌的僧人是否参预图像说书?敦煌讲唱文是否与口头演述相关?从以上情况看,对这一问题也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
在《从莫高窟6l窟{维摩诘经变)看经变画和讲经文的体制》一文中,我讨论过敦煌莫高窟经变画的讲唱特点问题,认为那些具有讲唱信息的壁画其实是对窟外寺院中的说唱经变画的模仿。因为根据敦煌所存的粉本,可以推测洞窟壁画有其寺院来源。由此看来,莫高窟那45000平方米壁画,至少其中相当部分,可以作为敦煌僧人曾参预图像说书的证明。因为这些壁画主体上是佛教壁画,它们必定是在僧人的主导下制作的。它们往往采用故事题材,因而必定同某种口头讲述相关。其中相当部分壁画有榜题,榜题大量使用了“时”、“处”等图画指示语,这些壁画必定对应于某种说唱。尽管敦煌洞窟缺少举行说唱活动的空间,也无足够的照明条件,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壁画却是对现实的说唱活动的反映。由此推断,图像说书(说佛经)必定是敦煌僧人的日常行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