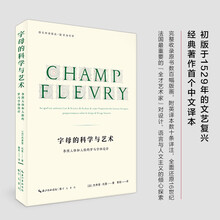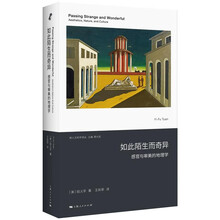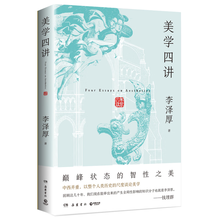阿多诺清醒地争辩道:“这不可能,也不应当。”(96)借助韦伯的范式,阿多诺认为:“艺术是将世界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那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强调艺术并不是使艺术回到“巫术”,因为,“艺术与理性化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于是,艺术的审美意念(通过模仿)与技术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就构成某种内在辩证法,即“内在于艺术的模仿与理性的辩证法”。(96)
那么,什么是艺术的模仿呢?阿多诺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说明:“被理解为主观创造过程与客观的、未安置的他者之间所结成的非概念性亲合关系。”(96)这是一种星丛式和解关系,而非同一性关系,既不可直接回归于自然,亦不可使自然“人化”。建构和解关系的模仿亦是一种“认知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亦是“理性的”。(96)
模仿超越了单纯的认知(原本的、工具意义上的),这样一来,艺术就摧毁了与知识相对的独特性与单义性,艺术于是被赋予了“综合”的功能:同时承担起了人面对世界的三重生存论关系。①正如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概念来解决生存性世界问题一样,阿多诺通过艺术同样实现了这样的综合。那么,艺术在历史上能否承担这类综合意义呢?阿多诺对此是抱有警觉的,他甚至谈到了艺术被毁灭的危险,而这种危机与艺术概念本身一样古老。因为认知取代了艺术成为主导原则,而艺术本身也面临被理性同化、操纵(文化工业)的危险,所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问题倒不在于艺术能否承担综合使命,问题在于艺术是否应该承担这样的使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