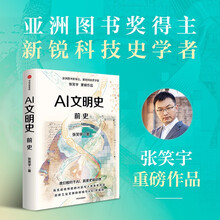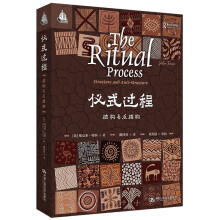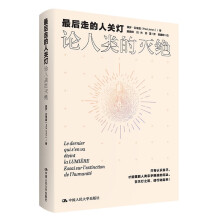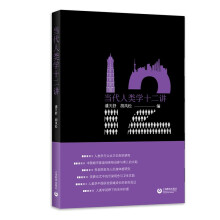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本书的三十位访谈对象,平时居于各地,许倬云在美国,金耀基、陈之藩、罗孚、倪匡在香港,李育中在广州,周有光、黄苗子、郁风、杨宪益、沙博理、吴冠中、黄永玉、丁聪、沈昌文、何兆武、高莽、汤一介、乐黛云、陈乐民、资中筠等在北京,贾植芳、钱谷融、徐中玉、何满子、方平、草婴、鲲西等在上海,辛丰年在南通,流沙河在成都。他们多经历了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既受传统文化熏染,又受欧风美雨影响,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br>今日世界又快又热,而文化大家渐行渐远,访问历史尤显意义深远。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他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思考,也是重温中国知识人那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