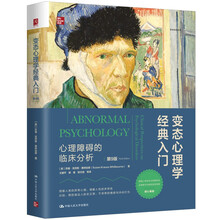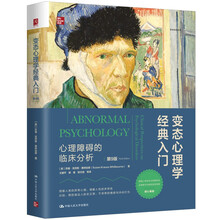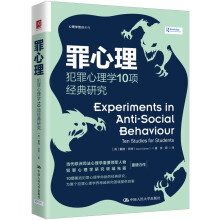序言一
序言一:艺术的治疗和我们时代的精神之“病”
文/朱其
艺术可以作为一种自我精神治疗的手段,也可以将之称作一种语言的精神拯救。在2006年,艺术家郭海平勇敢地尝试了一个行为实验,他一个人住进了南京的一家精神病院,该院叫“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他在这家医院与精神病人一起生活了三个月,并且教这些精神病人进行绘画和陶塑的创作。
在进行下面的叙述前,首先要界定一个核心词:精神病,这个词是否成立?目前精神病院收治的所谓精神病人主要指两类,一类是具有攻击性行为的行为失控者,对他人人身和财物造成伤害者;另一类是指不具有攻击性行为,仅仅是生活日常行为错乱并严重失范。
所谓“精神病”是指精神上有病的人。但精神上是否有病,实际上是说这个人的精神是否逾越一个时代大多数人所能容忍的行为底线。事实上,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时期,大多数人在某一个时代认为少数人精神有病时,往往真正有病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最终被逼疯或被监禁的少数人。在三十年前的文革时期,红卫兵疯狂批斗知识分子,狂热的崇拜毛泽东,上万人在街头游行跳忠字舞,这实际上才是一种集体精神病现象。而少数怀疑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则被认为是反革命和精神病,甚至被逼成疯子,而这些人在今天看来恰恰是真正精神健全的人。
人类精神是自由和多元的,精神在理想的意义上应该是一种灵魂自由想象和漫游的状态,人类精神向何处走都是它自身的一种选择,没有对错和正常与否。精神本身并不存在是否有病的问题,就像在文革时期,当大多数人认定少数质疑政治运动的人精神有病时,实际上真正精神处于疾病状态的是大多数人。所以,精神病这个词带有一种多数人的精神排他性的专制色彩,在中国成为了一个人格主体贬义词。
实际上,没有一种精神是可以称作有病的,只有精神不适应主流社会的失常者或者行为失控者。所以,我不赞成使用“精神病”或者“精神病院”这样的称呼,这实际上带有反人文主义的意识和立场。“精神病”称为“精神失常者”,“精神病院”称为“行为神经失控者治疗中心”,这样更为准确和人道一点。从严格的意义上,攻击性行为者和不具有攻击性行为者也不应该在一个同一个机构场所受到治疗,前者只是一种行为控制有问题,后者对他人行为没有伤害和攻击性,只是属于精神异常者,或与社会格格不入者,但这两者都不能将精神内容视为一种病,病症主要在于情绪和行为体系。精神病或者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性的政治概念,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科学称呼。
从精神本体说,每一种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每一个精神在他所处的时代可能会与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格格不入,或者实现方式上不能为现实社会所接受,这就造成精神异常者的行为反常,或者精神人格的问题,出现各种反常或超常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比如忧郁、妄想、臆念、痛苦、幻觉、紧张、语言错乱和行为失序等。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人巧取豪夺、抛弃人格独立、不断突破道德底线,这些人即使掌握了大量财富和权力,但实际上精神上是有病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急剧变化的伟大转折时期,实际上每个阶层的人都会有精神不适问题,上至高级官员、大企业家,下至知识分子、白领和底层民众。只不过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的严重程度、自我控制力和自我治疗的方式不同而已。尤其是现在中下层社会的人群,他们善良、诚实、遵守社会规则,但没有获得应有的经济收入和公正的社会待遇,工作压力、生活保障和就业竞争却在加剧,这使得很多人都产生心理问题,有些比较严重,但我们不能说他们精神上有问题,他们需要的是心理治疗。
在精神问题和精神治疗上,实际上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群体和治疗方式,即艺术群体和艺术的治疗方式。人类的艺术史和文学史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人文传统,这个传统从不将精神异常、反常、失常和超常的艺术家或作家看作是病人,而是欣赏这样的人,这个人文传统将这些人看作敢于越过人性在一个时代的禁忌底线的精神探险者,或者将这些人看作天赋的优异灵魂的持有者,他们身上具有常人没有的想象力、精神敏感和语言形式创造的天分,其中有些杰出者甚至被看作是精神先知、思想先驱或者伟大的哲学家。
尤其是到了近代,人类社会在政治民主、工业革命、商业和资本主义变革、城市文化兴起的伟大转变时期,权力、财富和资源重新分配,阶级和贫富分化严重,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和信仰衰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作家和诗人,但他们表现和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和人类集体走向的想象,批判现实和创造了新的语言世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精神失常和崩溃了,或者被认为是疯子、同性恋者,或者被送入精神病院。但这些人的思想和艺术语言已经成为今天普遍的主流文化或者大学课程的一部分,比如哲学家有现代性思想的先驱尼采、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阿尔杜塞、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艺术家有文艺复兴后期的卡拉瓦乔、后印象派的梵高、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意识流女小说家吴尔夫、德国新浪潮电影导演法斯宾德、中国朦胧派诗人顾城等。
艺术领域实际上像一个人类社会所谓“精神病”者的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个领域从不将精神异常或疯癫看作是一种病,而是将这些“精神病”者看作人类思想和艺术创造可能的精神探索者。即使在思想和艺术创造上没有天分的精神异常和疯癫者,也将艺术看作是一种精神治疗的手段。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哲学、文学和艺术也确实帮助人类从精神苦难和压迫中自我拯救,艺术可以使人类痛苦审美化,文学可以使混乱的自我经验叙事化,哲学则可以使自我对总体性的认识形而上学化,从而找到一个把握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和哲学都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精神拯救和自我治疗的途径。
郭海平在他“精神病院”内的日记中写道:“我现在主要精力是集中在以艺术的方式关注当代社会公众的精神问题”。这是一个当代艺术或者社会学领域非常有开拓性的课题。他在2006年12月5日的一篇日记还写道:“今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畏惧黑暗了。刚来精神病院,医院将我的住处和病人们使用的画室都安排在一幢住院病房的顶楼。刚开始,每到夜晚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四、五百平方米的整个四层楼只有我一个人,稍有动静,即使是走路都会有清晰的回音,为了减缓这种恐怖感,我总是打开整个楼层的灯光。二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地我开始关闭一些灯光,今天晚上我看到一间房间的灯还开着,我便去关上这个房间里的灯的开关,当灯光息灭时,房间里一片黑暗,这时我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舒畅,也就在这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开始喜欢起黑暗来,也许是巧合,我今天画的一幅作品的背景选用的也是黑色。”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到郭海平在深入“精神病”实施这项计划时,尽管他事先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是他的自我状态还是处在一种恐惧和探险的临界点上。即使他曾经有过心理医生的经历,他家族也有过类似的“精神病”患者,但在这段日子里,他这个算是与精神异常者有过接触经验的人,个人的内心还是走到了一个自我极限的边缘,但是他最终越过了这道界限,从而打开了一扇门,进入另一群被抛弃在社会边缘的人群的精神世界。在他深入的这个人群中,原先他只是想进入这群人的特殊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精神病”产生的社会背景,并且用艺术这种更人道的方式去治疗他们。但这次本来只是一个社会调查和艺术治疗课题的实验行为,很快使他产生了意外的收获,很多“精神病”的艺术创作像绘画、陶艺和诗歌写作,他们对色彩、空间形式和自我经验取材能力都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天赋。比如像崇拜机械装置的刘传军,他所画的机械装置绘画在色彩和空间丝毫不比正常的艺术家逊色,尽管他没有受过专业绘画训练,但他的形式感极强的机械绘画与法国怪异机器装置艺术家廷格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艺术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理性和日常性的工作,它强调的是与众不同的自我想象和超越日常的体验,艺术的杰出创造主要来自人的潜意识和超现实经验领域,这一点恰恰是“精神病”者的精神领域最活跃的部分,只是这个精神的无意识和绝对自我的部分没有找到社会表达的语言体系和接受形式。郭海平教会了不少“精神病”人画画、做陶艺和写诗歌,这些人实际上也不是被教会的,而是郭海平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潜质。德国著名现代艺术家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就是强调每个人内心世界实际上都有成为艺术家的潜质,只是有些人被现实意识压抑了。郭海平从这些“精神病”艺术家的作品中选出了一部分优秀之作,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精神病”艺术家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天分,很多作品如果以常人或者知名艺术家的名义展出,也许真的可以进入专业艺术展览体系。
我认为,没有精神痛苦和变态的艺术一定不会是伟大而深刻的艺术,伟大的艺术家一定是承受了远胜于常人的精神磨难,甚至达到精神崩溃,才可能产生杰出的语言创造。在二十世纪初,欧洲文化界开创性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在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探讨了艺术与精神无意识的关系,并形成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派、超现实主义艺术和诗歌,以及无意识自动写作等,精神分析学派的著名学者像佛洛伊德、荣格、拉康等,将自己的学说应用于艺术和小说的精神分析。佛洛伊德的一个开创性思想,是认为现代社会不应该歧视所谓的“精神病”人,他们实际上拥有比常人更丰富的想象和情感世界,尤其是他们的超现实幻想。“精神病”患者中的一部分人由于成为了艺术家和巫师,而在社会体系有了正常的生存角色,并转化了自我痛苦。而在现代社会,“精神病”人也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重新适应社会。
在艺术不断商业化的时期,郭海平的这项实验计划具有一种难得的探索精神。在这之前他还策划过一个题为“病:我们今天的艺术”的展览。他的这个计划实际上也可以看作这个展览的深入延续,但这次“祖堂山精神病院”驻扎计划更具有一种实验性和探索性,在形式和主题上也越出了一个纯艺术项目的界限,而是一个社会学、精神分析和艺术的一个跨学科实验。这个项目本身似乎很难界定一定属于社会学、精神分析还是艺术实验,但重要的是,郭海平的这个行为实验坚持将艺术转向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并且探讨人的精神拯救的问题,并且身体力行的闯入一个陌生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情。我们时代的艺术现在过于资本化、生产化和中产阶级化,在这个背景下,郭海平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真诚和勇气!
2007年7月21日写于慧谷阳光
序言二
序言二:疯癫从来就不是一种疾病
文/汪民安
在生活世界中,疯癫习惯于被看做是一种奇观,它是不幸对于少数人的悲剧性降临。正是基于此,在现代社会,人们投给疯癫者的是同情和好奇的目光。疯癫,使疯癫的观看者暗自庆幸,他们深感幸运,没有被某种神秘的魔力所掌控。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也历经过疯癫,甚至有时候还强烈渴望疯癫:事实上,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疯癫片断:或者酩酊大醉,或者被药物所催发,或者被某种激情彻底主宰,所有这些时刻,都构成短暂的疯癫经验:此时,人们甩掉了一切理性和道德的思虑,听任自然本性和冲动,屈从于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返归到一种原初的野兽状态。但是,在这片刻之后,人们会立即摆脱自己的野兽面目,洗刷自己的疯癫形式,重新回到彬彬有礼的生活常态――一旦酒精或者药物的功效失却,理性就会重新征服人们的身体。疯癫,通常就这样在人们身上昙花一现。这,实际上并不是疯癫,而是有关疯癫的短暂练习。
那么,谁是真正的疯癫者?只有那些具有特殊禀赋的英雄才能真正被疯癫降伏。不过,人们不应将疯癫看做是被动的结果:在人们看来,癫狂似乎是一种被压迫的后果,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外部力量将人包裹住,使得人们难以抒怀,于是,人在内心反复地挣扎,从而导致了疯癫。但是,按照尼采的说法,人一旦受到了压抑,表现出的不是疯癫,而是内疚和抑郁。这种自我折磨透过愁苦的面容一览无余。这正好是疯癫的反面。
事实上,疯癫不是内敛性的自我折磨,而是危险的不顾一切的外向性的爆发力量,它划破习俗和道德的漫漫夜空而愤然地伸张。疯癫者正是对理性世界的砸毁和藐视,才获得了自己的疯癫形象,这幅形象总是有一幅张狂的面貌。这正是疯癫者为什么有时候被看做是神有时候被看做是兽的真正原因:他们和这个理性世界完全而绝对的不相容――不是暂时的不相容。这正是疯癫者和醉酒者的差异所在:后者只是疯癫的片断,是疯癫的假面具。醉酒者的归途还是世俗的理性世界。而疯癫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神圣世界。这个世界和理性世界判然有别:疯癫者可以置理性世界任何的律法和秩序而不顾。对律法和秩序来说,疯癫构成危险,同时也正是这种危险,它们也招致了自身命运的劫数,它们通常被锁在高墙竖立的阴影之中。理性世界受到了疯癫的挑战,但它以禁闭的形式来迎接这种挑战。
疯癫世界,尽管经过了短暂的街头游荡,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关在逼仄的高墙之内,空间的闭锁只能遏制疯癫对理性世界的危险,并不能消除疯癫世界的自主神圣性――疯癫创造了一个没有物理空间的神圣空间,一个新的摆脱了理性世界的神圣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认为,疯癫者才是真正的欲望英雄。尼采就此说得更为明确:“一切生来不能忍受任何道德束缚和注定要重新创造律法的高人,即使他们实际上还没有发疯,也只能别无选择地让自己变疯或者装疯。”疯癫,为新生的思想铺平了道路。
就此,疯癫传达出来的是意志的无畏勇气。胆小和懦弱的人无法疯癫,它们总是被自我保存的本能所牢牢地禁锢住,而无法向理性世界毫无回旋余地地猛烈撞击。或许我们可以说,疯癫是主动意志的蛮干,它表现为一种巨大的抗争能力。在这种意志的抗争中,丝毫没有妥协的成分,意志决不会在任何的压力面前收手。意志逼得它的对手要么将意志毁灭,要么使意志不得不以一种疯狂的形态展示出来――正是这种意志的无理要求,使得疯癫者和小人区分开来。疯癫者是小人的反面,后者知道迂回,知道巧妙的掩饰,知道如何维持理性的平衡,在意志可能毁灭的情况下,小人会理性地后退,重新躲在安全的理性的庇护之下。只有疯癫者会奋不顾身,一举僭越理性的界限,闪电般地获得疯癫的永恒。在这个意义上,疯癫只会青睐少数人。就此,我们看到,渴望甩掉理性的人很多,但是成为疯子的人很少。醉酒的人很多,发疯的人很少。要想一劳永逸地摆脱秩序的桎梏,人们必须成为疯子。但是,不是每个急于摆脱生活桎梏的人都能变成疯子,即便是那些梦想成为疯子的人,那些渴望疯癫的人,他们要想获得疯癫状态,需要学习疯癫,需要对疯癫的反复练习,更需要神的眷顾。“主,请赐我以疯狂!只有疯狂才能使我真正相信自己!请让我的头脑谵妄,让我的身体痉挛,让我的眼睛看到稍纵即逝的光明和周而复始的黑暗;请让我在凡人从未见过的冰与火面前颤抖,让我在巨大的声响和无声的阴影中惊恐不安;请让我像野兽一样咆哮、哀鸣和爬行吧。”要让疯癫降临自身,有时候需要祷告,需要赐福。在一个理性主宰的文明时期,疯癫是上苍赠送给少数人的珍品。就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被疯癫眷顾的人中有如此之多的天才闪耀:荷尔德林、尼采、凡高和阿尔托。正是借助疯癫,他们闪电般在一个既定的理性世界中创造了自己的神圣世界。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创造自己的特殊世界的同时,他们也创造和习得了疯癫。
但是,这疯癫,却被理性世界看做是疾病――除了将疯癫看做是危险从而需要提防之外之外,理性世界还将疯癫看做是病态世界,他们要救治疯癫,试图让疯癫者重新返回到理性世界之中,就像让一个醉酒的人重新恢复他的清醒一样。就此,精神病院既是防御性的,也是治疗性的。为什么将疯癫看作是一种疾病?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理性建构了自己的合法垄断性,唯有理性,是人的正常而健康的确认标志。所有同理性存在着沟壑的人,都被看做是不正常的,是不自然的,是人的疾病形式。疯癫,或许是所有偏离理性世界的非理性类型中,同理性世界最相对立的一类形式。疯癫世界,当然会被看做是一种不自然和不道德的世界。在理性世界的眼中,疯癫是一种特殊的病人类型。要恢复自然而健康的秩序,要么就驱逐疯癫,要么就治疗疯癫――这正是文明社会中的疯癫的历史。问题是,在癫狂者的眼中,这个理性世界就是一个自然而健康的世界吗?这个理性世界不正是因为充满压抑而让癫狂者自己创造一个自主世界吗?这个癫狂世界难道没有自己的神曲?我们要问,在理性世界和非理性世界中,到底谁是疯癫?或者我们借用帕斯卡的话来回答,“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问题是,疯癫到底怎样展现自己的声音?谁又会耐心地倾听疯癫的置疑声?谁会领悟疯癫世界的神曲?理性世界将疯癫和医生置身于一个隐秘而封闭的空间中,医生能够随时撞见疯癫者的自我表达。但是,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些表达总是疾病的症候。医生借助这些表达,试图追溯疯癫者的病情根源。但是,如果这些癫狂者不是被看做病人,那么,这些表达将会看做是什么?
这正是郭海平新书的意义。同医生的看法不一样,在这里,疯癫者的表达,不是受制于一种内在的病情,相反,这些表达恰好是一种创造性本身。郭海平,医生和病人同时处在密闭的世界中,对于每个人而言,对方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对于医院而言,治疗总是要清除疯癫者的臆想,疯癫者只有消除了臆想,才是往健康的路上缓缓行进。与此相反,郭海平鼓励这些疯癫者臆想,他并不将疯癫者的自我表达看做是疾病的症候,相反,这些自我表达,这些充满奇思怪想的绘画,是疯癫世界的秘密:这些秘密无法被理性世界所洞穿。或许,艺术家是最接近疯癫世界的人。理性世界各类诡异的绘画,难道不正是疯癫欲望的隐秘表达吗?理性世界没有排斥这些绘画,只是因为这些绘画巧借了艺术之名。疯癫者的绘画,并不借助曲折的掩饰方式,这是疯癫者的自发创造,这也即是想像力本身。对这些作品,我们要作的并不是洞穿和破解其中的秘密,而是尊重和看护这些秘密,这些秘密是一个独特世界的抒情方式。现在,它聚集起来,以一种文明世界的运作方式,来到了我们眼前。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疯癫者的绘画?它和我们的知识如此地迥异,或许,它并不会唤起我们对它们的怀疑,而是唤醒我们对自身的世界的怀疑。这是怎样的怀疑?用福柯的话来作结束吧:“凡是有艺术作品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但是,疯癫又是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因为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
2007-7-5
自序
自序
文/郭海平
在我刚满二十岁的时候,我接触到一帮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思维和情感表达方式与我见到的其它同龄人明显不同,在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神采。我为之倾倒,也正是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便一直沉陷于这种“神采”之中不能自拔。有时我会认为这种“神采”就是一种生命的光芒,有时我也会认为这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种燃烧形式。
毫无疑问,这种“神采”使原本就不安分的我变得更加放肆和任性,同时,我也感到了某种莫名其妙的惶恐和不安。我与这帮艺术家很快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从此,我与他们一道也开始神采飞扬了起来。我们标新立异,我们无拘无束,我们尽情享受着自然生命的活力,热情,癫狂,痴迷,奔放。这一切让我的青春岁月残酷而难忘。
也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我对艺术与人之间的异常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精神层面上,艺术家和精神病人无疑具有某种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极为特殊的一群。所不同的是,艺术家得到了社会一定的包容,而精神病人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排斥和压制,常常成为人们歧视和排斥的对象。其实,对于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常态,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人性,又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生活的正轨,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我常为之困惑不已。
有资料证明,在“疯狂”与“天才”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疯子与天才只有一线之隔。像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巴尔扎克、凡高、蒙克、伍尔芙、乔伊斯、叶赛宁、庞德等等都常常成为人们例举的对象。
在我的经验中似乎只有那些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只有那些不甘平庸、喜欢在自己精神世界里沉醉和畅游的人,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并在心理上留下障碍,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上便形成了某种错乱的病态表现。
有意思的是,在精神病医学尚未出现和尚未进入中国以前,不少艺术家就曾将“痴”、“癫”视为一种境界,如顾痴(顾恺之)、黄大痴(黄公望)、倪迂 (倪云林)、梁疯子(梁楷)、米癫 (米芾)、癫张醉素 (张旭、怀素)等。其实,这与西方社会理解的精神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文人的疯癫大多数都是受主观意识的控制,对此,我们会常常见到后人用“佯狂”和“佯疯”来描述他们疯癫。事实上,在那些特定的年代,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这种“佯狂”和“佯疯”的方式才能逃避道德、法律和政治方面的限制和迫害,并从中谋取一些有限的精神自由,这也可以算作是中国文人在压力面前的一种独有智慧。而在西方,我们很少见到装疯卖傻的艺术家,像凡高、蒙克等人都被医学确诊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的崇高地位,也丝毫没有影响公众对他们艺术创作的欣赏和喜爱。遗憾的是,多数国人仍将精神疾病视为是一种不光彩的精神残疾,精神病人和他们的精神世界仍然被主流社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事实上,像凡高和尼采这样的精神病人已注定成为历史,这是因为,今天的法律、医学和道德已难以容忍他们的再次出现。但我依然坚信,自由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挫折与对抗中才能得到体现,但在多数人眼里,自愿选择“挫折”和“对抗”的人很可能就是人的一种病态的表现。这些年,我的精神状态一直在病与非病之间徘徊。我的精神世界有时变得脆弱而敏感。我亲眼目睹了周围亲朋好友乃至家人在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故。我终于发现我已经不能遵循正常人的生活,我无法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结婚生子,上班下班,过着规规矩矩的正常人的生活。现实中,我也常常对自己的不正常产生怀疑,这时,似乎只有艺术才能够帮助我摆脱这些困境。
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直吸引着我,同时也让我常常感到困惑。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家印刷厂的设计室调到一家政府主办的心理咨询机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接触到许多寻求心理支持和帮助的青年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性中挣扎的种种表现。我发现精神疾病其实早已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所谓病态其实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它促使我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思考病与非病、健康与不健康,道德与非道德,正常与不正常,意识与潜意识和无意识等等问题。为此,我邀请了多个领域的专家成立了“艺术分析部”,期望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解答。但最终我还是把希望投向了艺术创作的实践,因为我对艺术与人精神之间的那种紧密联系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领悟,或者说,只有进入艺术创作的实践,我才能真正领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精神“障碍”和“疾病”。
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停止在艺术上的探索。有一天,我在画画的实验中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是一种类似于电流穿越全身的感觉,或许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是一次全身心的瞬间体验,正是这种神秘的体验感受让我放弃了手上的其它工作而做出了做一名全职艺术家的决定。对此,很多人并不能完全理解,甚至有人认为,这又是一次带有病理特征的不同于正常人的决定。从那时开始,我尝试了各种自由开放的艺术表现方式,除了绘画,我还涉足摄影、装置、行为艺术等等。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视野,我参与了多个展览的策划,期望与更多的艺术家和公众形成更为开放的互动。与传统的绘画和心理咨询实践相比,当代艺术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互动过程,我非常享受这种互动的过程,从中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这也许就是一种人的自由的实现和健康生命的具体体验。
2005年我邀请了27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围绕着“病”的主题在南京美术馆举办了一场“病:我们今天的艺术”展,在这个展览画册的前言中,我试图对近2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状况进行一个整体的理性反思。我认为,近20多年来中国的先锋艺术中,“病”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其表现是十分充分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伤痕艺术”[注1]到90年代初兴起的“玩世现实主义”[注2],然后再到21世纪初“青春残酷”[注3]主题的兴起,其大量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病”的主题。过去,大家之所以不愿正视,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病”与“美术”理念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许与中国人讳疾忌医的传统习性有关。我之所以选择“病”作为主题,是因为这些年的所见所闻使我对“精神疾病”有了更为痛切的感受。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反思和关注这些问题,用艺术的方式介入这一主题,这应该是我对精神疾病和人的自由问题思考的另一种延续。
2006年,我认识了江苏康曼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聂鹰先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慷慨帮助,我才如愿以偿地住进了依山傍水的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我实现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精神病人的愿望,并最终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精神病人艺术创作的计划。应当承认,我们对精神病人文化及其精神世界的研究要远远落后于西方许多国家,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精神病人仍然并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即使是医疗系统,关锁式治疗[注4]仍是我国大多数精神病院对精神分裂症病人施行的普遍治疗管理方式。而早在一百年前西方社会就出现了弗洛依德这样的精神病研究大家,尤其是法国艺术家杜布菲[注5]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精神病人的艺术逐渐受到公众关注。通过对这些艺术作品的欣赏,公众对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为生动和具体的认识。今天,法国、德国、瑞士、巴西和美国等许多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展示精神病人艺术的博物馆,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已经成为人们探索人类心灵和潜意识的重要渠道。我与聂鹰先生交谈最多的内容就是力争在中国建立第一座“精神病人艺术馆”[注6],以改变国人对精神病人存在的种种偏见。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多方面的努力下,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精神病人的权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始建于1952年10月,它坐落于南京市著名的南郊风景区内。祖堂山有着漫长的建寺历史,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最后两个皇帝死后就埋葬在祖堂山山脚下,著名的“弘觉寺”与精神病院也仅仅只有一墙之隔。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安排。皇帝陵墓、寺庙与精神病院,三者均与出世和人的灵魂有关,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神秘之手相牵。郁郁葱葱的丛林、沁人心脾的空气、飘荡在夜色山谷里打更的声响,让我有种跨越时空之感。在实施整个计划的三个月里,我们为病人们提供了油画、丙烯、水彩、彩色铅笔、油画棒、陶土等多种艺术工具,但由于参与这项活动的一百多位男女病人(全院七个病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绝大多数都不曾有过绘画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无法适应各种绘画材料属性的特殊要求,如很难掌握调色中应当遵循的擦笔、洗笔、换笔,以及轻重缓急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用油画棒画画就成为大多数病人的首选,再加上他们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和药物的干预,他们的作品便呈现出了自身特有的意味。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共完成了三百多幅(件)作品。通过对他们创作过程的细心观察和分析,我从中获得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体验与领悟。
大多数住院病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自信”,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表现出十分的谦卑和温顺,这一点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精神病人的“疯狂”正好相反。但很快我便发现他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集体的“不自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精神病药物和医院的特殊环境的持续作用。正因为他们普遍表现出极度的不自信,使得大部分病人很难介入到我们为他们安排的艺术活动中来。在我接触的一百多位病人中,主动要求参与艺术活动的只占极少比例。大多数病人需要的还是不断地鼓励。相比之下,那些住院时间不长的病人,则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参与热情。本书介绍的作品大部分属于这两种类型的病人所作:第一种是生命力和意志力特别顽强的病人;另一种则是属于住院不久的病人。
但不管平时多么谦卑和不自信,一旦拿起画笔,大部分病人都会表现出相当的独立、坦诚和自由。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不少人都没有我所预想的那些心理障碍。他们随心所欲,他们自由自在。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们常说的“真实让你获得自由”。极度的不自信和极度的自信就这样奇异地交织在一个人的身上,由此形成了另一层意义上的精神分裂。
习惯于从高空俯瞰事物,这是我观察到的精神病人作画的一个独特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视角,我认为至少可以反映出他们经常具有这种特殊的俯视体验,这是一种飞翔在天堂中的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精神运动状态,这也许是精神药物的作用,也许这就是精神病人对世界的特殊感知方式。这一发现立刻让我联想到中国当代艺术眼下正在盛行的“升天”、“飞翔”、“飘”、“登高”和“俯视”的画面,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这些艺术家的精神也出现了某种与精神病患者相似的体验。艺术家、精神病人、现实、超现实和自由等等文化概念在我头脑中又一次陷入到了无法理清的混乱状态。
这一次住院的体验,使我对精神病医学、精神病人以及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等问题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受。从社会设定的角色看,我是以一个健康的艺术家的面目出现在病人们面前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却又更愿意与那些被称之为是病人的患者为伍,这不仅仅是因为情感,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内在精神的相通。在观察精神病人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一切渐渐又会聚成了一个全新的没有头绪的谜团。为了表达住在医院的种种感受,我除了以日记的方式来记录每天观察的结果与心得之外,也经常会在病人们都离开画室之后便拿起画笔来表现我内心深处的特殊感悟和感受。在这批绘画作品中,无数扭曲的形体挣扎着相互缠绕、相互交织在一起,他们也许是从黑暗中蓬勃而出的生灵,他们挣扎着,相互纠缠在一起,(见图147、148、149)其实,在那一时刻,我发现挣扎、纠缠的不仅仅只是他们这些住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这一次住院的体验,也让我对精神病医学、精神病人、艺术、以及灵魂等问题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受。我感受到了当今精神病医学的欠缺和浅薄,也感受到了精神病人内心的那份悲哀与凄凉,同时我也隐约感受到人的灵魂的存在和艺术对人精神关照的无限可能性。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公众在欣赏精神病人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去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今天现存文化的真实处境。
这次深入精神病医院的艺术实验活动得到了医院领导的热心支持,他们不仅为我和病人们提供了宽敞的艺术活动场所,同时还从紧张繁重的医疗第一线抽调担任过男女多个病区主任的王玉女士协助我开展工作。王主任一方面要负责自己病区里大量繁忙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我这里的每一步进程,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王主任共计病倒了五、六次。正因为有了王主任细心周到的安排和介绍,才使我与病人之间最终实现了非常完美的合作。
为了让读者和观众更好地把握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我与王玉分别撰写了“艺术评述”和病人的“病史及临床表现”。另外,我还邀请了国内著名当代艺术策展人兼批评家朱其博士和著名文化学者汪民安博士为本书撰写了前言,我相信他们的介入一定能够弥补我的许多缺陷与不足。朱其博士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十多年来,他对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和走向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汪民安博士则是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的著名学者,不仅如此,他在中国当代艺术理论领域也有着较高的声誉,他的专著《福柯的界线》是让中国读者走进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优秀启蒙读物,眼下,他的另一本从全新的视角研究尼采的专著又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我确信,有了上述三位专家学者的支持,这本书的文化艺术价值一定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借此机会,我对他们的热情帮助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2007-4-27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