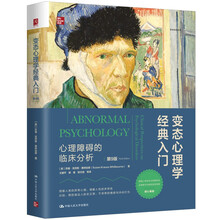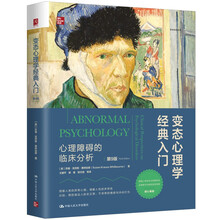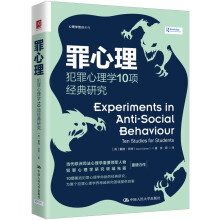现在,成瘾问题肆意横行,创巨痛深。即便我们自己没有深受其害,我们认识的人中也总有人为一种残忍的强迫冲动所驱使,试图靠改变大脑功能来重塑个人体验。这种普遍而残酷的冲动给个人和社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后果。在美国,12 岁及12 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6% 的人符合物质使用障碍的标准;此外,死亡人数中约有1/4 是死于用药过量。每天,全球约有10000 人死于物质滥用。这条通往坟墓的道路上,还伴随着令人痛心疾首的丧失:丧失希望、尊严、亲密关系、金钱、生育力、家庭和社会关系以及社群资源。
放眼世界,成瘾似乎才是最可怕的健康问题——在14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 人中就有1 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单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成瘾问题造成的财政花销不仅是艾滋病的5倍多,还是癌症的2倍。也就是说,在美国,接近10% 的医疗保健支出都被用在预防、诊断和治疗成瘾性疾病的患者身上。在其他多数西方国家,这一数据同样骇人。尽管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和人力,但相比50年前,患者成功康复的概率并未有所提高。
药物成瘾的代价如此广泛、深重而持久,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过度使用的问题非常普遍,几乎稳固地存在于各个地域、经济层级、种族和性别。治疗也存在很大的阻力。尽管很难得到可靠的估值,但大多数专家认同只有不到10%的成瘾者能长期戒断药物。从治病的角度而言,这一比率低得出奇:脑癌患者的存活率都比这高1倍。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前景黯淡,但也还有一些理由或能鼓舞人心。有些成瘾者曾几近走上绝路,但最终成功戒断了药物,一直没有复用,甚而重新过上了健康有益的幸福生活。虽然神经科学尚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转变背后的机制,但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例如,我们知道成瘾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包括遗传倾向、发育影响和环境输入。我说错综复杂,是因为这些因素中的每一项都非常难解。换言之,它们无不涉及成百上千的基因和数不清的环境作用。而且,这些因素还相互依存。比方说,某条特定的基因链可能会增加成瘾倾向,但前提条件是还要存在(或不存在)其他特定的基因,以及在发育阶段(产前或产后)置身某些特定环境,有过某些特定经历。因此,虽然我们已经对此颇有了解,但这种疾病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仍旧无法预测一个人是否会成瘾。
虽然有多少成瘾者最终可能就会有多少种成瘾的途径,但所有强迫性使用都遵循大脑功能的一般原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分享这些原理,进而从生物学上揭示物质使用和滥用走入的死胡同,即:再多药物,我们也永不满足,因为大脑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基本上是无限的。曾经的常态不时被使用药物后的高峰体验打断,最终势必会转变成一种唯有药物才能暂时扼制的绝望状态。理解了成瘾者的体验背后的机制后,便不难看出除了死亡和长期戒断,再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平息在每次暴露的间隔期内产生的那种要命的渴求。等到行为完全受病状左右时,大多数成瘾者会在妄图满足那永不满足的欲望中死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