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德鲁克开创了管理学这个学科,属于现代管理学的开山鼻祖的话,那么查尔斯·汉迪则沿着德鲁克开创的思路继续前进,探究组织和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当今社会的个人提供了应对严酷的组织的强大压力的精神依据。德鲁克告诉你组织是什么和为什么,汉迪告诉你面对组织时个人该怎么办。德鲁克关注的是体系,查尔斯·汉迪关注的是人本身。《汉迪作品:觉醒的年代》是查尔斯·汉迪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查尔斯·汉迪对管理界的贡献颇丰。他以"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未来工作形态"的新观念而闻名于世。主要贡献包括:
自雇工作者
适当的自私
联邦制组织
三叶草组织
3I组织
甜甜圈原理
四种管理文化
中国式契约
S型曲线
权力补贴(逆向授权)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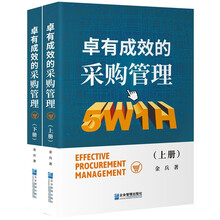


如果说彼得·德鲁克使管理登上大雅之堂,汤姆·彼得斯将其推而广之,那么查尔斯·汉迪则赋予了管理所缺失的哲学的优雅和雄辩。
——领导力大师 沃伦·本尼斯
汉迪的著作深得我心。组织的基本模式将如何发展,工作生涯的未来将会怎样,对于这些重要问题他都给出了深入浅出的精辟回答。阅读他的著作是我生命的里程碑,他的观点深深震撼了我。
——管理大师 汤姆·彼得斯
汉迪总是如此的优雅,他是管理领域真正的大家,在世界众多的管理思想家中堪称翘楚。
——《从优秀到卓越》《基业常青》作者 吉姆·柯林斯
查汉斯·汉迪:喜用比喻的管理大师/斯特凡·斯特恩,FT中文网·《金融时报》
三叶草、空雨衣、公文包、大象和跳蚤:在过去30多年里,查尔斯·汉迪借助他的书籍及其标题,不断探究英国语言的隐喻潜能。现在这项工作还在继续。
这些意象的确引人入胜,而且总有一种严肃的深层用意。作为一位“管理大师”,汉迪并非汤姆·彼得斯那种喜欢炫耀的人。他说话声音没那么大,没那么戏剧性,但却不乏坚定。
在汉迪新出版的《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对话式回忆录中,他回顾了一生中启发他写下管理和组织方面著作的种种经历。
他把焦点放在生活中的重要瞬间,来阐明一些更深刻的主题。因此,我们很快就能把他生命中的重要时期串联在一起:英裔爱尔兰教区牧师的儿子、攻读希腊哲学家思想的牛津大学生,后来为壳牌公司招募大学毕业生而驰骋于东南亚地区。
书中也勾画了其他重大事件:与引人注目的伊丽莎白结婚、脱离壳牌、创立伦敦商学院,以及投身自由作家的“公文包生活”。
所有这些事件都支持着书中提出的各种建议和见解。虽然汉迪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但仍有更多的经验可以传授。
他回到经典著作中,特别是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eudemonia(通常被译作“幸福”)概念,希望从中获得灵感。但是汉迪说,这个词“更好的译法是‘尽情盛放’,或者是尽最大努力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有趣的是,这个概念也用于组织机构中,只是现代商业大师们称之为‘优化核心技能’。我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解释。”
不幸的是,很难用“尽情盛放”来形容战后时期的许多英国企业。汉迪在探究许多曾经辉煌的英国企业毁于一旦的根源时,对这个问题的感悟很有意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英国管理人员都受军队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一时之间,英国企业热衷于类似军官食堂的做法,管理人员可以享用有3道菜的正式午餐,而低级别的人只能将就着吃盒饭……但商业组织的运营环境却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发号施令的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而且商业组织不能指望别人会自动接受权威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
汉迪认为,英国工业表现不佳的另一个根源在于会计职业的主导地位。直到汉迪及其同事开创了对英国企业老板的正规管理教育之前,在各种职业中,只有会计师能够夸耀获得了公认的正规培训。
“为会计师提供的会计培训并没有错,”汉迪写道,但是,“会计职业却意外地成为了英国的商学院。”汉迪的言下之意是,会计师可以告诉你花了多少钱,但不应告诉你该花哪些钱,以及怎样花。
汉迪说,一个给人印象更深刻的关于组织效用的理论可以在剧院里找到。节目单把每个人的名字列出,而不论他们的贡献有多么微不足道。“演出公司不会把演员称为人力资源——要是这么做,就没有演员会为他们工作了……‘经理’一词只用于管事(而不是管人)的人。”
节目单上最瞩目的位置让给了与顾客直接沟通的人:演员。而且他们所接受的是指导,而不是管理。事实上,导演在剧目进入轨道后就退居幕后。
身居导演这个职位的人相信演员们可以独立完成剧目,而演员们往往能在导演离开后对剧目做出改善。“信任带来激励。”到最后,真正重要的人会提供直接反馈。
这正是汉迪的长处:仁慈、体贴且严肃。实际上,他喜欢自称为“社会哲学家”,奉行“常识的学术研究”。他愿意看到企业致力于变得更好,而不必变得更大。管弦乐队或葡萄园需要每年扩大规模吗?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
“组织不是机器,”汉迪写道,“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活生生的团体。要描述它们,我们需要使用团体的语言和个人的语言。”别把事情复杂化。“管理不是什么神秘或概念上难以理解的东西,”他写道,“难就难在理念的运用,而不是理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