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188-1965),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生于东京一米商家庭。谷崎的创作倾向颓废,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小说世界充满荒诞与怪异,在丑中寻求美,在赞美恶中肯定善,在死亡中思考生存的意义。他的散文世界则洋溢着浓郁的日本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与民族的风情。 代表性有短篇小说《恶魔》(1912)、《春琴抄》(1933),长篇小说《痴人之爱》(1925)、《卍字》(1928)、《细雪》(1942~1948)、《少将滋干之母》(1950)、《钥匙》(1956)、《疯癫老人日记》(1962),随笔评论集《阴翳礼赞》等。他的《源氏物语》口语译本(1934~1941)文笔明丽酣畅。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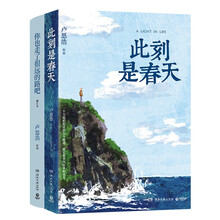








应谓渠先生之邀,着手日本近代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的散文、随笔的选译已历时一年左右。刚刚接受任务时内心颇为矛盾,深知2000年对我来说各种任务纷至沓来,再加砝码,实感吃力;但是,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对我很有吸引力。不要说他的小说杰作,就是那些如行云流水的散文、随笔也很使人心醉。于是,我还是承担下来。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习惯,我一边选读谷崎的大作,一边对他那些在东西文化之间探索,并将自己独特感受诉诸笔端的作品情有独钟。这些作品不仅可读性很强,而且谈得入情入理。
我曾经在多处谈过我对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一得之见:“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其文学发展过程中都是在与域外文学的矛盾、融合中而创新、发展。同样,作为个体的作家亦是循此规律前行。”谷崎润一郎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更是如此。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吉田精一所说:“日本文学乃至于近代思想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东洋与西洋如何调和或者说交融的。”(见《夏目漱石全集·别卷》,筑摩书房,15页)
试如所知,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在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东西文化(文学)激烈碰撞的时点,各种思潮纷至杳来。主张全盘西化,“脱亚入欧”者有之,作为它的反拨倡“国粹主义”者有之,有人主张将日语用英语取代或者用罗马字母取代日文,有人则固守日本传统文化,俨然是民族的卫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森鸥外、夏目漱石为代表的作家、学者则选择了一条既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改造、激活本民族文化,同时又时刻注意坚持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来过滤、选择异族文化的方略。森欧外在《鼎轩先生》中的一段话最充分地表述了这一主流方向。他说:“新日本是处于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交融的漩涡的国家。这里既有立足于东洋文化的学者,也有立足于西洋文化的学者。但他们都属于一条腿的学者。”“但是,时代要求另外一种学者,即要求把东西洋文化各作一条腿站立的两条腿的学者。”这些话,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谷崎润一郎(1886—1965)虽然被称作“唯美主义”作家,但是,他整个创作也是在东西文化探索中前行的,只是不同时期表现不同而已。
谷崎润一郎跟小说和汉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升入国民高等学校学习之后,谷崎的恩师稻叶青吉在汉学方面给予了他极大影响。“这位先生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是很有朝气、上进的青年,经常将一本自己喜欢读的书揣在怀里走进教室。他的读书范围涉猎儒教、佛教,特别是对阳明礼学和禅学格外倾倒。从汉文学到平安朝、江户时代的文学及和歌、软文学作品均很热中。他不仅给学生讲王阳明、柴田鸠翁、铃木正三、西行、卡莱尔的作品,还讲《经国美谈》、《椿说弓张月》等小说,并且奖励把《太平记》《风月物语》等作品的优秀段落能够背诵的学生。”谷崎润一郎从十二岁至十六岁时在先生的这种很自由的教育方法的熏陶下,点燃起了对文学热爱的热情火焰,特别受到先生的宠爱,“一直到进入中学之后,还经常拜访住在芝的稻叶先生的家,受其指教、熏陶。”1899年他十三岁时,还在日本桥附近的贯轮吉五郎的秋香塾接受汉文素读训练。在1918年和1926年他两度访问中国,与郭沫若、周作人、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他创作的《麒麟》(1910)《玄奘三藏》(1917)、《鱼、李太白》(1918)、《苏州游记》、《中国游记》、《秦淮之夜》、《南京奇望街》(1919)、《西湖之月》(1919)、《庐山日记》(1921)、《上海见闻录》、《上海交游记》(1926)等作品都是取材于中国典籍或以中国为舞台而写作的小说和纪行文。谷崎润一郎在日本近代作家中是位对当时中国文坛比较关注又比较熟悉的一位作家,特别是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事业尤为关心。虽然他对中国文坛的了解不能说很深刻、全面,但对有些问题确实有独到见解,和其他日本近代作家相比是高出一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