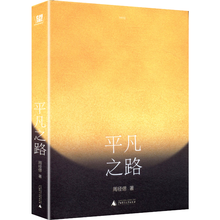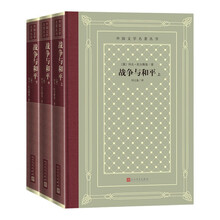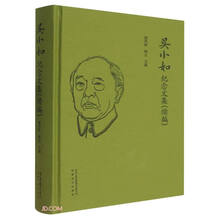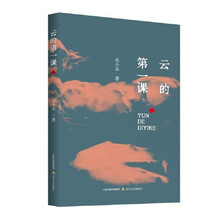我看朱德当主角
杨学武
朱德总司令在电影《太行山上》第一次当上了主角,我看后既感到喜出望外,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以往凡有老一辈革命家出场的影视片中,朱老总总是“老人组合”中的老配角。他紧跟在老主角的身边,一副笑脸相迎、憨态可掬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个人特写好像就是那个“叉腰做报告”的镜头。作为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总司令,却从来没有机会表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将风度。我因为非常崇敬和爱戴朱老总,曾经暗自为他打抱不平:既然是堂堂三军总司令,为何不能在与他有关的影视片中当主角?
大凡读过一点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朱德在中共历史上的卓越功勋和崇高地位,因此不需我在此为他“歌功颂德”。毛泽东曾有句名言:“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如果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朱的地位即使不在毛之上,也应该与毛“平起平坐”。从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中共在党内会议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挂着两幅画像:毛主席、朱总司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广场上和全国人民高呼的是两个“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其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朱毛”都是中共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朱德为何长期以来“反主为客”呢?个中之因,也许众所周知,但无人敢说破。于是有人便拿朱德的个人品德来说事,认为朱德的“配角意识”源自他的“伟大谦虚”。对朱德的谦虚,有人归结为他的“农民本色”,有人归结为他的“儒将风度”,还有人归结为他的“赎罪情结”。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
朱德是当主角还是当配角,似乎是他的个人意愿,其实并非他个人做得了主的。而且我认为,朱德是一个名垂千古的历史名人,他的角色如何定位,似乎不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乎历史的真相和公正。朱德是民众和历史公认的主角之一,究竟为何不能当主角呢?民众有权知道内情,历史应该说明真相。
由此我联想到另一位应该当主角而曾几何时连配角都当不上的张闻天。他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长期以来在中共的文件和报刊上,他的角色是不伦不类的“负总责”。直到1979年中央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才首次公布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可后来中央党史有关部门找到一份经陈云确认的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其中又说张闻天是“负总责”。于是有人找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要她同意在张闻天的生平履历上去掉“总书记”职务。刘英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便据理力争,经过艰难求证,终于弄清了张闻天当选总书记的由来。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念张闻天百年诞辰的文献记录中,开头的一句“关键词”就是写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任总书记”。可在无可置疑的史实面前,党史研究室的一位负责人竟然还在审查该片时,提出要在遵义会议这一段加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一句话。刘英明确表示“不要”,“因为这是写张闻天的片子,没有必要加。”她还大发感慨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引自2005年第10期《炎黄春秋》)
刘英为张闻天力争“总书记”的角色,当然不是一个妻子为自己的丈夫“谋私”,而是出于公心为历史负责。而且这样的事情,不仅刘英要争,我等之辈的民众也要争。因为历史是属于民众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朱德终于也在影片中当上主角了,他和张闻天一样成了历史的“幸运儿”。不过我从《太行山上》看出,朱德这个主角当得并不怎么“名正言顺”。导演似乎担心朱德的主角戏太重了,会出现“有人往哪儿摆”的问题。于是专门为“不出场的角色”安排了几出“重头戏”:一是让朱德把“朱毛”的习惯叫法更正为“毛朱”;二是让朱德当者罗荣桓的面“表忠心”:“我朱德这一辈子跟过三个领袖,蔡锷、孙中山、毛泽东,跟着毛泽东是我最好的选择。”这几出戏虽然只是“小插曲”,可分量特重。我等观众一看就明白,朱德这个主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角,而是一个“前台上的主角”。
朱德担任总司令几十年,逝世至今也二十多年了,如今好不容易才得到一次在电影中当主角的机会,可这个主角似乎当得又有些勉强和窝囊。于是我想,如果他九泉之下有知,是感到可喜,还是感到可悲?
(原载《杂文月刊》2005年第12期上)
“球形典型”的回归
符号
去平遥古城,返程顺道看了大寨。40年前共和国的农业圣殿,经领袖号召、行政发动、媒体推介,一时成为举国朝拜的去处。那时通往昔阳路上是川流不息,有如“文革”中的大串联。有人开玩笑,光取经者们排泄的粪便,也够为大寨增肥献宝的了。而那里生产的,已不是粮食,而是成囤成仓的“经验”!看当年大小媒体的报道,大寨经验已远不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举凡“政治挂帅”、“斗私批修”、“阶级斗争”、“割?本主?尾巴”、民兵武装、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妇女家庭方方面面,都是出有经验的。用当时一位领导的话说,大寨是个“球形典型”。典型而呈“球形”,是借用了物理学的原理。球表面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成为整个球的支点,让球立住。大寨“球”的任何一点,都会变换出令人羡慕的经验的。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经验终于销声匿迹了。拔高了大寨又回归到她应有的位置。
四十多年过后,大寨又如何呢?当年无缘亲炙其光的笔者,仍然产生一种想撩开她今日面纱的冲动……直到来到这里亲自观看与听介绍,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么赫赫有名的大寨,不过七百多户人家;驰名中外的虎头山,也不过五百来亩土地。当年竟然生产出那么丰富、完美、成熟、动人方方面面的经验,真是每寸土、每根草,都成了经验的结晶。
“典型”一词,在前苏联文学中是颇为走俏的。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不止于文学,实录的新闻报道也是奉为圭臬的。于是为某种需要而进入“高大全”误区,其结果可以想见。“球形典型”的信奉者满以为“样板度”愈高,则影响力愈大。常常接二连三、连篇累牍,排炮式地催“球形典型”问世,让人由起初的惊异,到倾慕,到最后的疑惑,到厌烦厌恶。
不必责备“笔杆子”们的一哄而上铺天盖地,受指派的使命与刚性任务的下达,是他们施展才干难得的机遇。当采访资源近于枯竭时,他们只好“另辟蹊径”寻求新的支点。于是有着许许多多支点的“球形典型”,就这样“横空出世”。
然而当时间与实践的针将“球”戳消了气,到头来则只能证明那不过是一只轻飘飘的气球。所谓“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其实是“掺水”、“拔高”的虚夸。不论在公众、在民间、在私下,人们在内心深处是并不认同的。毕竟绝大多数人是天然的唯“物”唯“实”主义者。
让人痛心的是“球形典型”带来严重的“殃及池鱼”后遗症。一次遭愚弄,久久存戒心,是难以治?的心理硬伤。既然曾经浪费了多次的“感动”,自然要产生持续的“抗药性”逆反。每遇“典型”即无论真假好次,先要“条件反射”式地打上大问号,要进行戒备式的审视,冷峻的甄别。心存芥蒂地嘀咕道:真这样么?
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表明几十年问我们确有一批真典型、好典型,至今仍高高矗立,深入人心;也毋庸讳言,一批假典型伪典型,也让人们伤痛犹在记忆犹新,其中不少早沦为笑柄。令人担忧的是时至今日,“球形典型”的嗜好与思维模式依然可见,有可能继续为害社会。
如今当我迎着夏风立在虎头山,以亲历者的身份俯瞰大寨,“河东河西”的沧桑感扑面而来。有意思的是,五百亩狼窝掌如今已不再生产粮食而改作了森林公园。尽管眼下不够浓郁,但黄土地上这或浓或淡的绿意,使人对大寨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
大寨人如今已将挖煤等重体力活交给了外地的民工;自己则从事着服务旅游的第三产业,出售包装精致的小米、玉米,手工缝制的鞋底、手帕;在窑洞里开饭馆,用特色的南瓜、玉米棒、自制的饮料,招待天南海北的客人。他们自己也告别了当年的那些“经验”。
典型也者,“型”是不可以轻易“经典”化的。是什么样,就该是什么样,任何生拉、硬贴,人为、强求,都是徒劳的。倒是那种不怎么“经典”、不那么成“型”的典型与经验,倒比较容易接受公众与时间的“安检”的。
行走中,一辆带“8”字号车牌的新奥迪蓦地驰到了眼前,好熟悉的一张面孔走下车来,这不就是长白、长胖了的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么!原来她是专程前来接受香港凤凰台的采访的。不久又一阵风似的离开回她的昔阳去了。目送远去的车影,我又有一种“球形典型”终结的回归感。
(原载《四川文学》2005年第12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