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猪听着音乐挨宰,比起棍棒齐下、人喊马叫地将猪抬到肉案上,吓得屁滚尿流,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我总觉得还要看此举的动机如何。如果是推己及人(猪),替猪考虑,彰显天理和人道,那么,这种做法就令人钦敬;但如果还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像给孔雀“壮阳开屏”一样,那么,此举的真诚感人程度就大打折扣。因为随后我就在这则报道的中间,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因为屠宰前烦躁、惊恐的猪甲状腺会大量分泌,同时会大量失水,影响肉的质量。”
看起来这和“人道”、“猪道”、天理、慈悲都没有关系,不过是为了屠宰以后的肉更加可口。反过来说,如果猪在挨宰时的惊恐、烦躁不会影响肉的质量的话,那么就不会让猪死到临头还听音乐?问题是猪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面对绳索、棍棒、明晃晃的刀具,它怎么能做到不“惊恐”、不“烦躁”,视死如归?这家屠宰场给出的答案是,让猪听音乐。而听音乐的目的仅仅是让它忘记作为一个生命最本能、最直接的反应:嚎叫或竭力挣脱,然后从容就义。
那么我的问题是,对猪来讲,究竟是清醒而反抗着死去好呢,还是被人麻痹,蒙在鼓里,至死不悟好呢?简单地说,就是对于人做的播放音乐这件事,在上帝眼里,是视为善、还是视为恶呢?是更人道、更符合天理和公义,还是更残忍、更虚伪、更不可饶恕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那只被宰的猪的话,我不愿不明不白地死去。我的生命哲学是“即使徒劳,也要抗争”,如果敌人有一天必得置我于死地,那么我愿意像我崇拜的英雄威廉·华莱士(电影《勇敢的心》)一样,吐出爱者赠送的最后一滴麻药水,歌尽而亡。
这就是现代环保的悖论,人与自然的二律背反。也就是说,就人目前的进化程度而言,还根本无法脱掉动物的自私性。尽管他的智慧可以高度发达,但他的肉身仍然不过是生物链的一极——因而我们所想的,我们做不到。
比如,我们因为沙尘暴的袭击,而禁止滥伐森林;因为酸雨的降临,而禁止向空中排放毒雾;因为捕鱼的需要,而不许向河流倾倒垃圾;因为治病人药,而不能将老虎和麋鹿杀尽……那么,反过来就是说,如果没有沙尘暴,我们就可以滥伐森林;如果不下酸雨,我们就可以向空中排放毒雾;如果有鱼吃,我们就可以向河流倾倒垃圾;如果身体健康,我们就可以将老虎和麋鹿杀光。而依据佛家“众生平等”的原则,人不能屠杀、伤害别的物种,不是因为这些物种“珍稀”、濒临灭绝,而是人根本没有资格和权利践踏别的生命,不管它对自身有益还是有害。
如此说来,笔者反对该文作者的观点仅仅是因为他举的例子太少太没有代表性,似乎只要多数直言者获荣了,就能高奏一曲政治文明的凯歌了?否!问题的本质已经凸现出来了,直言者的荣辱云云,“辱”,来自何处?荣,又来自何处?从根本土说,不都来自在上者的赐予吗?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自由说话是天赋人权,直言也好,不直言也罢,张口便说就是了,管他什么获荣抑或受辱!在这样的社会里,所谓直言者获荣,绝对不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闻,更不会被摇笔杆的人抬出来作为衡量政治文明的秤。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走向依法治国的路途中,而我们一些呼唤政治文明的人却根深蒂固地有着一种“恩赏”的观念,这实在是让人悲哀的地方!
究竟什么是“政治文明”?在当下的语境中也许并非一个适合谈论的问题,而且按照逻辑常识,对一个事物下肯定的判断也颇为不易,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先讨论一下“什么不是政治文明”的问题。且让我来抛砖引玉,我的一个最简单的否定判断是:“恩赐”不是政治文明。
向一家晚报的时评版E—mail过去一篇稿件,很快收到他们的一封自动回信,其中强调了该版对来稿的要求:“热点、理性、建设性,谢绝杂文。可以批评,但不要讽刺。”读后不禁愕然,继而释然。
报刊时评的勃兴,是近一两年来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时评一向被视为“报屁股文章”,在那些或以含蓄的曲笔见长,或练就了一手“不着一字,尽显风流”功夫的杂文家眼里,这种有话直说、就事论事的文体无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不想时易时移,风水流转,如今报刊上时评栏目和版面遍地开花,而杂文的阵地却大有日渐萎缩之势。笔者在媒体混饭有年,既摆弄过杂文,也划拉过时评,对二者如此这般的消长盛衰颇为不解,不想上述那家晚报时评版对作者投稿“可以批评,但不要讽刺”的要求,却令我茅塞顿开。
中国古代有所谓“讽谏文学”,但讽谏者不过是以讽刺之名,行建议之实,有点儿像鲁迅在《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中说的新月社诸君子,“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收入《古文观止》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和《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是讽谏文学的两篇代表作,你看邹忌为了让齐威王明白“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的道理,不惜大长他人(徐公)志气,大灭自己威风;司马相如为了规劝汉武帝不要亲自打猎,不惜一唱三叹渲染铺陈,以求“于悚然可畏之中,复委婉易听”之奇效。严格地讲,讽谏追求的是“曲学阿上”,故不能算是讽刺,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讽刺。自杂文在鲁迅那个时代成为文学的一个主流样式,讽刺就被锤炼成了杂文的一件主打武器。讽刺者要么嬉皮笑脸,要么指桑骂槐,要么骂人不带脏字,要么“杀”人不见血,总之是上上下下没个正经,“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不是摆出一副比被讽刺者高明一·百倍的样子对他指手画脚,就是一上来就旗帜鲜明地站在被讽刺者的“对立面”拿他当逗乐开涮。被讽刺者如果没有那种“被打了左脸接着还让打右脸”的非凡雅量,在饱受嘲笑、奚落甚至谩骂之后,很难不对讽刺者产生强烈的反感和刻骨的敌意。培根说, “当长于讥讽的人使别人对他的机智感到敬畏时,他就必然对别人的记性有所戒惧。”同理,当长于讽刺的杂文家使某些被讽刺者对他的“险恶用心”感到愤恨时,他就必然对被讽刺者的耐性有所戒惧。于是杂文趋于边缘化,不少杂文家转而操作时评,虽大异其趣,似亦不妨苦中作乐。
时评中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则不然。批评者一般不玩讽冻那一套迂回曲折的手法,而是诚恳忠直,温柔敦厚,恨不得把自己的一颗红心掏出来让被批评者过目。他们有时也脾气火爆,言辞激烈,但却立场坚定,态度端正,善于设身处地地从被批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与被批评者一道,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克服困难,应对危机,把共同的事业建设得更加美好。北京人到某个地方办事,喜欢用“咱们这儿如何如何”的句式来和人家套近乎,那意思是说,别看我是来求你办事的,其实我和“咱们这儿”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如果给“咱们这儿”添了麻烦,您也就当是“咱们这儿”自己的麻烦,多担待着点儿。与此类似,批评者在小心翼翼地批评“我们的”有关部门在某项工作中的不足,诚惶诚恐地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一定少不了要反复声明“我们的”有关部门一直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有效措施……
当“他们的”讽刺成为禁忌,“我们的”批评遂生意兴隆。与厚颜无耻的溜须拍马和声嘶力竭的歌功颂德相比,“建设性”的批评得以郑重其事粉墨登场,已经要算是不小的进步。然而眼见杂文作为一门讽刺艺术竟然日渐式微,又不免对这一进步心有不甘。笔者这两年一再撰文,呼吁在中国大力推行与被批评者“誓不两立”式的“恶意批评”,现在看来,我实在过于天真了,当务之急恐怕是要将以杂文为代表的讽刺艺术从这场莫名其妙的灾难中拯救出来——毕竟讽刺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好意,却未必怀有多少恶意,离“恶意批评”尚有百里之遥。
于极权者来说,这种“全体一致”的好处更可用来表明自己的受拥护程度达到了“百分之百”。这样一来就一切都变得无可置疑了——因为我“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因而这种“全体一致”充当的是种道具的作用。
这种“全体一致”又可达到“震慑”的作用。你看,我的民众对我的拥护率是百分之百,所以与我作对就是与我的国民过不去,将直接与我全体国民成为对手。这是挟一个民族之力向外示威,以让对方不能不掂量再三,从而达到自保的目的。此时的“全体一致”依然是充当道具的作用。
但有一点却也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就是这种表面上的“全体一致”其实不是真正的“全体一致”。我们从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可以看到,那些平时总是“全体一致赞成”与“百分之百拥护”者,在最后关头却都不“赞成”不“拥护”了——他们都放下用来表示拥护的枪支逃跑了,也就是抛弃了平素口口声声要效忠的“领袖”。这也正是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领袖”没想到“连衣服都背叛了自己”,而平时这“衣服”曾是多么的“贴心贴肺”!所谓“全体一致”最终被证明不但是欺人且是自欺的把戏。愚弄他人者最终为他人所愚弄。欺人者最终也被人欺。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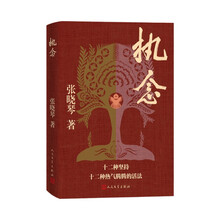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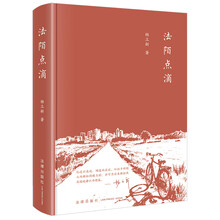
这是我第二次编选杂文的年选本, 从编辑思想来说, 与上次并没有什么不同,仍然较多地考虑了作品在思想上所具有的启发性。
现在做杂文年选本的不止一家。对读者,能够在不同选本间进行选择是一件好事情。对编选者,选本多应当存在一个竞争性,但我反倒有一份内在的轻松。
每一个做编选工作的人,都会面临“选尽佳作”的压力,而事实上“选尽佳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且哪些作品算佳,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选本多了,遗珠之恨自然就会减少,这样,我也不必因为“选不尽佳作”而伤太多脑筋:
这好像是一个偷懒的想法,别人的工作哪能作为你轻松的理由?但我认为,杂文选本多了, 当我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做的时候,就能够心安理得一点。我不必患得患失, 既怕丧失选本的特性,又怕遗漏了别人眼里的名篇。
杂文是表达思考的文体, 而不是仅仅表达一下态度的短章,这是我对杂文的一个看法。近两年里,随着报章上刊载越来越多的“时评”,我的这种想法更加顽固。
时评的兴起,正在改变社会的舆论生态,人们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民间的声音迅速壮大。但至少在现阶段来看,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也已经出现。大量“时评”已不是社会与时政评论,而是“据报载”的粗放写作。“据报载”写作的大量出现,既显示了媒体在制造公共话题上的力量,也使相当多的时评人被引导成单调的“读后感”写作者,他们几乎不须注意身边的事务,真实的生活不再成为他们写作的来源,原发性的生活思考和社会观察现在已经相当稀少。时评人是最爱读报的和上网看新闻的人,那是他们感慨的源泉,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被报道,那也就相当于不存在。
议论的对象都是来自于“报载”,最初这也许是一种写作与发表的技巧,一种应对干预和莫名其妙的麻烦的策略,然而现在它成了时评写作的“法律”。一些报章声明,所有时评必须根据报道来写。报章已经把时评圈养在“据报载”的园地之内了,这不仅提高了审读中的安全系数,还使文章获得了“时效性”。你可以忽视生活,但不可忽视“报载”,“时评法”规定了, 生活经历没有时效,也没有评论的由头, “报载”才能使评论获得时效和由头。于是大量报纸执行着“据以评论的报道必须在三天之内”的规定, 时评写作进入了 “时效竞争”的阶段,思考已经不重要了,正像痢疾症患者,吃了就拉,不需要胃肠,有直肠运动就行了,是否能在看到“报载”的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
发表的门槛已经调低,这本来很好,但怪的是表达的上限也同时设定,根据“时评法”,所有人只能直接说话,不能直接说的,也不能以间接的方式说,不得意在言外、不得曲径通幽,这一条执行起来很严。于是我们又看到,最快速度的直话直说到处奔流,在不同的事由中, 同样的意思在反复地进行平面复制,新的祥林嫂运道好极了, “不过脑子”的速度竞赛制造了写手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