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帘中冲进了龙眼。他目睹着屋里的一切。“我的孩儿,你过来,过来。”妈妈浑身是土,嘴角沾了血,躺在只有一半席子的土炕上。他盯着妈妈,她只是不语。窗外大雨瓢泼一般,下得好痛快。妈妈感激地望着大雨。龙眼坐在炕沿上.妈妈拦住他的腰,抚摸他的白发。龙眼紧闭着嘴。妈妈不知从哪儿摸出了药丸和那一点点酒。她揉碎了一个药丸,蘸上酒给龙眼涂起来。.好孩儿听话,搽上这药头发就变得锅底一样了。“一丸药涂完了,白头发变成了红的。龙眼两手紧紧抱住了头,皱着眉。“孩儿怎么了?“妈妈,我痒!”你咬住牙关,孩儿。“我痒!我痒!”龙眼叫着跳起来。父亲正和方起吃着皮冻,望着雨水。突然龙眼往前一扑,两手狠狠地扼住了父亲的脖子。刘干挣甩着头颅,方起抱着拳头击打龙眼的手腕,龙眼的手渐渐松脱了。龙眼妈出来了,一下跌倒在地。刘干挣跳起来,回身摸起了烧火棍,掂了掂又换上切菜刀。龙眼死死盯着父亲的刀子。刀子掉在地上。妈妈的脸惨白惨白。龙眼擦去妈妈嘴角的血,扶她坐下,然后向屋外大雨中走去。“我的孩儿呀,你往哪跑呀……”<br> <br> <br> 书摘1<br> 也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庆余在小土屋里捣鼓出了奇迹。<br> 她把一块碎裂下来的瓷缸瓦片凸面朝上支起,陶盆里的瓜干黑面已经闷了半天,用水调弄得不软不硬,散发出微微的酸甜。瓦片下不紧不慢地烧着文火,金祥一把接一把往空隙里扬麦糠,大股浓烟呛得他泪流满面。火苗儿蹿起来,庆余就用脚碰他一下,他赶紧抓一把碎草屑儿压上。庆余用食指蘸一点唾沫描一下光滑的瓷瓦面儿,吱的一响。她伸手挖一块面团,在手中飞快地旋弄旋弄,然后左手抓一块油布擦擦瓷面儿,右手迅速地把面团滚一遍,一层薄薄的瓜面粘在了瓷瓦上。她赶紧取起泡在水里的一块木板,用钝刃儿在那层瓜面上刮。刮呀刮,刮呀刮,瓜面儿实实地贴在瓷瓦上,接着干了,边儿翘了!她用杀羊的长把刀插进翘缝,像割韭菜一样哧哧两下,整张的小薄饼儿就下来了,比糊窗纸还薄。这些黑色的美丽的薄饼一会儿摆成了一尺高,金祥在一边拣碎的边边角角吃。一陶盆瓜面都做完了,小土屋里有了整整两大摞子小薄饼。庆余像做针线活儿一样盘腿坐下,左手取薄饼,右手的杀羊刀一按一折,刷刷两下,叠成了长方形。那个快哩!金祥快要乐疯了。一会儿两大摞子薄饼都折叠完毕,庆余四仰八叉地躺到了地上,累得呼呼喘。金祥这才明白,叠饼这活儿慢不得,因为饼从瓷瓦上刚取下是艮的,略一停就脆了。这活儿得赶个艮劲儿。金祥问:。年九妈,这是什么饼?”庆余闭着眼:<br> “煎饼!”<br> 瘦长的年九第一个叼块煎饼跑上街头,震动了全村。谁见了都问,问过还想咬咬。年九让他们尝,他们嚷:“哎哟这个脆呀!哎哟这个香呀!”正喊着金祥提着裤子踱出来,嘴里照样叼个煎饼。人们说:“该死的金祥啊,好东西都让你家吃了。日你妈的金祥!”金祥只是笑,使劲提一下裤子,伸手取了煎饼,拔一棵大葱剥剥皮,又揪一个辣椒,一块儿夹在饼里,吭哧吭哧吃起来。年九吃过了煎饼,像蛇一样缠到金祥身上,说:“爸吔!”大伙儿一阵感慨:“吃着黑煎饼,搂着痴老婆,人家金祥过的才算日子!”一个老婆婆说:“快别说人家痴了,不痴的人也没见做出这么好的饼来。”大家都不做声了。了不起的庆余,她传过来的手艺使一囤囤的瓜干有了着落。庄稼人一块石头落了地,禁不住长舒一口气。接下去的问题就是快快跟庆余学会做煎饼,一刻也不耽搁。街上的人跑来跑去传递消息,连赖牙一家也破门而出。人们挤到小土屋门口,有的从小后窗往里望着。大黄狗和脏女人庆余都在熟睡,黄狗果真趴在炕上的一摊破棉絮上,巨大的鼾声不知来自哪个。人们嘭嘭嘭敲窗擂门,两个都不醒。有人一迭声地骂,老黄狗才声如洪钟叫了一声,慵懒的女人接着啊啊地舒展吐气。门开了,黄狗夹着尾巴闪到一边,庆余挠着痒儿探出头来。“不过年不过节,串门的来这一大些。”她半睁着眼咕哝一声,又仰脸看看日头。有人拨开她往小屋里挤,四下里瞅,终于发现了瓷片刮板什么的。那个人用木板敲着瓷片跑出来,说好一个庆余大痴老婆,用这几件破东西变戏法一样变出了黑煎饼。众人呆呆地看,像瞅一宗神物,不言不语。金祥奋力夺了抱回屋子,骂得很难听。年九又取一个煎饼吃起来,凹凹的脸儿盛满了自豪。<br> 大约过了两个月,每家每户都有了会做煎饼的人。了不起的吃物啊,庄稼人有了发明创造了。这功劳自然而然归到了庆余身上,也归到了收留她的金祥身上。后来庆余才告诉男人:在南边黑乎乎的大山后边,人人都会做煎饼。那里人做这个才叫熟哩,一人烧火同时又能摊饼调面——油布放在大脚背上,一手添糠末捅火,一手端起湿面团,大脚一甩油布飞上来,接住一擦,面团按上去滚动……一眨眼工夫就完成了。那里的人半天工夫能摊二百四十张煎饼,且无一张破损。那里的老老少少都吃煎饼,牙口好的吃脆的,没有牙的用水泡了吃。出山走远路,背上摞煎饼走百里,十里地吃一张。煎饼里夹葱又夹韭,有钱的地主夹肥肉,咬一口,直流油,小姐、丫环捶后背。金祥乐得摇着脚板,在老婆饱胀的胸部理了一下。年九学金祥一样伸出手去,被他踢了一脚。庆余说:“该。”她又说南边摊饼可不用破瓷缸片,都用平底儿锅,那是过生活的宝物啊,叫“鏊子”!天哪,鏊子鏊子,怎么不早说味!金祥搓搓手,说他起早贪黑走长路,翻山越岭也要背回一个鏊子——天底下还有这样古怪物件!他说到做到,第二天。往腰上捆了一摞煎饼,鸡叫第一声时上路了。<br> 如果知道这是一条怎样漫长、怎样崎岖的路,金祥也就不会走了。可怜五十岁的金祥,靠树叶和瓜干长成的骨肉,没有多少耐力的金祥,就这么背着一摞子煎饼上路了。背上凸出的饼使他看上去像个罗锅,地势愈走愈高,他越发要弓腰而行。渴了就喝洼地上积的雨水,饿了反手抽出一张煎饼,去路边偷一棵葱夹在饼里。有一次被人逮住了,南边的人野,揪住他的衣领狠狠揍,金祥在地上滚着,煎饼撒了一地。揍他的人用脚踩着踢着满地的饼,说:。屁饼。”金祥死命地抱住那人的腿,连连说“行行好”,这才没让人家把煎饼全踢碎。他流着泪收拾一路的食,眼花了,辨不清与泥土一样颜色的煎饼,最后连土块一起装在背袋里,往前走。背后的人笑骂:“鲠鲅!”金祥一怔,加快了步子。天哪,这里的人也跟俺叫鲠鲅,俺还没有走远哪。他头也不抬地赶路,心想翻过那一座座山就差不多到了。他走过一个小村就要问一遍:“有鏊子吗?”人家说没有,他只得继续往前走。有时他想起了老婆庆余,心一阵狂跳。她和年九留在家里,还有个黄狗。夜间进去歹人怎么办?金祥一双手不禁颤抖起来。后来他想出家人不挂家,反正着急也没有用,不如忘了她,把她从心窝那儿赶开。他这样想着用巴掌在胸前一捋,说一声:“呔!”就把她赶跑了。他果然觉得轻松许多,眼前也清亮了。不知走了多少个日夜,他又开始问:“有鏊子吗?”人家说:“俺没听说有那种鳖东西!”金祥走开了。他心中已经把那种圆圆的平底铁器想得神圣起来,觉得像个没见面的老友。闪闪发光,他们一见面就会认得出,说起话来。“嘿嘿,鏊子。”金祥念叨着往前赶路,终于进山了。从没见过这么高的石山,他觉得长了见识。一想到庆余也是从这样的路上走来,并且还要照顾那条黄狗,他就想那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了不起哩。”他说着,揉揉眼从背上取煎饼吃。<br> 这是条让金祥记一辈子的路,是一个人只能走一遭的路。<br>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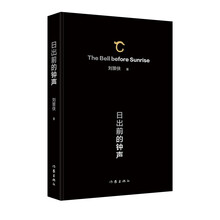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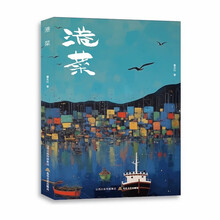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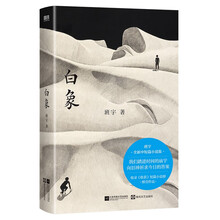
我极想抓住那个。瞬间感受”,心头充溢着阵阵狂喜。我在其中领悟:万物都在急剧循环,生生灭灭,长久与暂时都是相对而言的;但在这纷纭无绪中的确有什么永恒的东西。我在捕捉和追逐,而它又绝不可能属于我。这是一个悲剧,又是一个喜剧。暂且抑制了一个城市人的伤感,面向旷野追问一句: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些又到底来自何方?已经存在的一切是如此完美,完美得让人不可思议;它又是如此地残缺,残缺得令人痛心疾首。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熟知的世界,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原来那种悲剧感或是喜剧感都来自一种无可奈何。
心弦紧绷,强抑下无尽的感慨。生活的浪涌照例扑面而来,让人一拍三摇。做梦都想像一棵树那样抓牢一小片泥土。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这永远只能停留在愿望里。寻找一个去处成了大问题,安慰自己这颗成年人的心也成了大问题。默默捱蹭,一个人总是先学会承受,再设法拒绝。承受,一直是承受,承受你的自尊所无法容许的混浊一团。也就在这无边的踟蹰中,真正的拒绝开始了。
这条长路犹如长夜。在漫漫夜色里,谁在长思不绝?谁在悲天悯人?谁在知心认命?心界之内,喧嚣也难以渗入,它们只在耳畔化为了夜色。无光无色的域内,只需伸手触摸,而不以目视。在这儿,传统的知与见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神游的脚步磨得夜气发烫,心甘情愿一意追踪。承受、接受、忍受——一个人真的能够忍受吗?有时回答能,有时回答不,最终还是不能。我于是只剩下了最后的拒绝。
二<br> 当我还一时无法表述“野地”这个概念时,我就想到了融入。因为我单凭直觉就知道,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人可以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
我沿了一条小路走去。小路上脚印稀罕,不闻人语,它直通故地。谁没有故地?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绺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
我又看到了山峦,平原,一望无边的大海。泥沼的气息如此浓烈,土地的呼吸分明可辨。稼禾、草、丛林;人、小蚁、骏马:主人、同类、寄生者……搅缠共生于一体。我渐渐靠近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故地指向野地的边缘,这儿有一把钥匙。这里是一个入口,一个门。满地藤蔓缠住了手足,丛丛灌木挡住了去路,它们挽留的是一个过客,还是一个归来的生命?我伏下来,倾听,贴紧,感知脉动和体温。此刻我才放松下来,因为我获得了真正的宽容。
一个人这时会被深深地感动。他像一棵树一样,在一方泥土上萌生。他的一切最初都来自这里,这里是他一生探究不尽的一个源路。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他的激动、欲望,都是这片泥土给予的。他曾经与四周的丛绿一起成长。多少年过去了,回头再看旧时景物,会发现时间改变了这么多,又似乎一点也没变。绿色与裸土并存,枯树与长藤纠扯。那只熟悉的红点颏与巨大的石碾一块儿找到了;还有荒野芜草中百灵的精制小窝……故地在我看来真是妙迹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