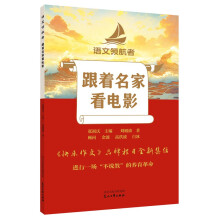外面有一个人在叫我,我出去了,那是房东处惟一的小徒弟,房东开着油漆店,专为雇主刷新屋子的。<br> 他很矮小,看去也不过十一二岁的光景,头大得很,怪可笑地摆在他狭小的双肩上。肚子大得凸出来,腿因之更显得细小可怜了。虽然我见过他不止一次,我却从没有仔细地瞧过他的脸,趁着和他对面的机会,我仔细地打量了他。<br> 脸和全身相反的生得很可爱,红红的唇,小小的牙齿,鼻子也很端正。但脸上的表情却痴呆的,相仿于白痴脸上那种木然的傻样。<br> 他全身都沾满了各色油漆的斑点,连头发上也疏落地粘着。<br> “你是找我的吗?”我问他,看着他仿佛完全不动的眼睛。<br> 他瞧着我,瞧了有一分钟之久,半晌,才含糊地应了一声,随即用手指着房东的住处。<br> 我发现他的眼睛很大,而且黑白分明。我伫立着接受他的凝视,我又觉得他似乎没在看我,像把眼睛停在我身上,而心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一样。<br> 我的邻居们都从房东那儿学得了对他的歧视,大家奚落他,无事时拿他开心,叫他“木头疙瘩”。据说是他比傻子还不中用,有的已经搬进来三年的住户,都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说他平日就会偷嘴吃,什么都作不了的。<br> 我却没从他脸上找到他们跟我说过的他的丑样,相反地我倒觉得他很好看。我想他若是洗净了脸上的泥垢,穿上干净的衣裤,一定比房东的胖少爷还体面的。<br> 我跟在他后面向房东的屋子走,几次他都落下来,站在侧面瞧我,像瞧一个怪物似的细细地瞧。<br> 我心里充满了不能言说的狐疑,我觉得奇怪又好玩,我想他是不傻的,要是傻,也一定是跟大家公认的傻不一样的傻法。想着,我慢慢地挨近了他。<br> 这时候,我们院中的最爱说笑的李大嫂跨进大门来,一手提着系在一起的几个茄子,另一只手里握了一个小小的油瓶。<br> “买菜去啦?”我招呼她。<br> “是,还没做晚饭哪!”她回答我。<br> 接着,她把左手里的几个茄子使劲往我身边的小徒弟头上一抡,嘴里笑骂着:<br> “你这个傻王八蛋,你也知道大女学生好,跟我走你怎么不这样往近靠呢。”说着,哈哈地笑着,又找补着:<br> “您可别见怪,他大婶。”<br> 我只好笑着,瞧着她带着她响亮的笑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br> 他的头上留下了两个茄子的小小的紫色的刺,他并不拂掉它们,连用手摸摸额角都不,像完全没有被茄子打过一样。<br> 我倒十分过意不去,原来是我挨近他的,他倒挨了无辜的抡,虽然茄子不是什么坚硬的东西,但那样大的圆球,总是有相当分量的。<br> 我怜惜地为他拂去额上的茄刺,就便替他掸掸额上的积土。<br> 他也往我身边靠着,但又怔忡的,用疑惑的眼睛细瞧我的脸,嘴里发着含糊的声音,迟疑地承受着我的怜恤的抚摸。<br> 我扬起我的手帕,预备用力地甩甩从他发上沾下来的土。就在我扬手的那一瞬间,他像一只野兔那样敏捷地从我胁下跳出去。<br> 我惊愕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瞧他在墙角保护似的蜷曲着他有着大肚子的小身子,想他也许以为我也是要打他才跑开的。真无怪大家都说他傻,实在是不懂事,我觉得又可气又好笑,又觉得他傻得可怜,这样蜷曲着,头固然是不要紧了,可是腰和屁股不都还可以任人自由地踢么?<br> 我过去,拉起他的头,他不抵抗,只用力地闭紧了他的眼睛。<br> 我只好不耐烦地叹着,等着他自动地站起来,他一定是被责打得失去他可怜的辨别力了,不能明白什么是爱抚和责打在动作上的区别。<br> 我们这样可笑地相对地蹲着,半晌,他偷偷裂开一只眼睛,一瞧见我,又急急地闭上。我消去了适才觉得好笑的心情,心里只有怜恤和奇怪。我尚不十分清楚他的生活,只知道他的工作是给其余的工人提油桶而已。我搬到这里来也不过刚一个礼拜,我想他或许是受雇于房东家来作杂活,因为过度的贫穷,所以不得不在这忍受着凶悍的女主人的苛苦的待遇。也许已经是无家可归了,无从脱离这长年伴着油漆的日子。<br> 房东太太一脸横肉,厉害是远近知名的。<br> 他一直蹲着不动,我装着不在意地把脸转过去,我一转开脸,他便睁开眼睛瞧着我,像一只洞里的老鼠瞧着洞外的猫一样。<br> 我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消去他对我的惧怕,我想抚摸他,又怕他在我抬手之间逃去,拉他,又怕他误认为打。我想这样继续蹲下去一定是对他不好的,他主人既然打发他出来办事,一定愿意他快办好了回去。晚了,凶悍的房东太太能轻轻地放过他吗?<br> 我想我还是继续保持着不动手的姿势好,我竭力在我脸上作出最和善的样子,但我不正面看他。<br> 果然他像安心了,慢慢地站起来,脊梁贴着墙,眼睛不瞬地看着我,而且一点一点地挪开他的身子。<br>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轻轻地,轻得像一只猫,我依旧蹲着,像完全没看见他一样,但我偷偷地用眼睛追随着他。<br> 他转到我背后去,我直觉到他的眼睛凝固地瞧着我的背,很久没有移开。过一会,我听见他走了,慢又轻地走去。<br> 正在我要旋回身子来的时候,我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吆喝,夹杂着肉击撞着肉的清脆的响声。<br> 我立刻站起来,转过身去看。<br> 他的肥大的女主人站在他的面前,他正一如刚才我见过的那样蜷曲地蹲下去,闭着眼,左颊上红红的。<br> 我瞧着房东太太的横脸,不知是为他说情还是装着没看见他好。我们所有的邻居都是不以为他的被责打为意的,甚至有人还说:“打!该!打死也不多。”这样助虐的话。有时实在瞧着他被打得太厉害了的时候,便都躲避地走开,让他们主仆去自己了他们的账。<br> 幸而房东太太注意到了我,她走向我,而且向我微笑着。平日我是很少和她说话的,她笑,我无端地心慌,她不至于赖我留着她的小徒弟,耽误了她家的工作而对我大发威风吧。<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