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道统论的社会思想背景
(1)社会上士庶的对立和统一
唐代的山东士族,要用周礼来规范现实政权,这个目的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为唐宗室所属的关陇贵族集团并不肯就范。唐太宗通过重修《氏族志》、禁止士族内部通婚等办法,来打击山东旧族,就是很显著的例子。史称他崇儒,其实不过开设馆阁、学校,优待经生,以听政之暇跟他们讲论一番而已;他用儒生,也只因为这些人读的书比较多,所谓“多识前言往行”,能为他提供历史上的得失而已,并不以礼教的实施为其政纲(当然,某些时候口头上不妨
这样说说)。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的抗拒。皮锡瑞《经学通论·序》:“唐时乃尊周公为先圣,降孔子为先师……岂非经学不明,孔子不尊之过欤!”先圣、先师是太学里立的尊位,先圣是最高的,先师是配享的,这个制度出自《礼记·文王世子》,并不指定是谁。汉儒的说法也纷纭不一。但皮锡瑞以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来批评唐代“孔子不尊”,则颇为失考。以周公为先圣,自是东汉以后古文经学的提倡,并不自唐始,相反,是在唐终了。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云:“汉魏以还,或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或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显庆以后,从房乔等议,始定而不改。”检史册,方说近实,皮说失考。《旧唐书·儒学传》、《贞观政要·崇儒学》及《唐会要》卷三十五,都说贞观二年诏罢周公先圣,以孔子为先圣。(《新唐书·儒学传》作“六年”,误。)《会要》所载最详,此举是出于房玄龄的建议。后来高宗永徽时,曾经复以周公为先圣,但到显庆二年,便由长孙无忌建议更正。从此以后,孔子的先圣地位便不再动摇,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夕。所以,皮氏讲的“孔子不尊”,只是
唐初数年而已。
尊崇周公,自是士族礼学家起的作用,但太宗近臣房玄龄与妻舅长孙无忌并不肯就范,抬出孔子来相抗。唐初修《五经正义》,也、发生过冲突,结果由太宗的托孤大臣于志宁等人来最后审定。看来,唐初关陇集团颇具操纵能力,对于士族既用之又抑之。
至于庶族知识分子,唐朝中央政权对其崛起是很有扶持之功的,科举取士是制度上的保证,而唐太宗提拔马周、刘、自等人,也很显出将政府官员从功臣贵族转为一般文士的企图。他的后代也有类似的态度,《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彭景直要求在祭奠山陵的礼仪上“择古作法”,受到了唐中宗的驳斥:“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显然,他对礼的态度与庶族文人相似。当然,大批地提拔进士出身的庶族知识分子,是武则天的基本国策。不过,武周革命时,因为士族子弟守礼沉正,不大肯依附诡从,而隐存李唐,所以复辟以后,清检礼法的门风又为世所重,唐政权也改变了打击政策,改为拉拢了。但庶族阶层已经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了。这样,当严格的礼学家与高谈尧舜的文士们针锋相对时,中央政权必须有强健的操纵力,一手“抑浮华”,一手“尚通脱”,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开、天盛世的景象。
安史之乱以后,强健的中央政权一失,矛盾便无法被控制,而呈互相攻击的局面。杨绾、贾至论科举,认为进士的浮薄是致乱的祸根,而李华作了一篇《质文论》,认为繁文缛礼才是无可救药的弊病,直是反唇相讥。中唐以降,士族旧门与庶族新贵已是两支分庭抗礼的政治队伍与社会力量,形成党争,而学术流别亦随此而分。
然而,两者在政治目标上却有着一致性,那就是扶助唐室“中兴”,加强中央集权,削平藩镇。因了此种一致性,尧舜之道与周公显庆二年,便由长孙无忌建议更正。从此以后,孔子的先圣地位便不再动摇,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夕。所以,皮氏讲的“孔子不尊”,只是唐初数年而已。
尊崇周公,自是士族礼学家起的作用,但太宗近臣房玄龄与妻舅长孙无忌并不肯就范,抬出孔子来相抗。唐初修《五经正义》,也、发生过冲突,结果由太宗的托孤大臣于志宁等人来最后审定。看来,唐初关陇集团颇具操纵能力,对于士族既用之又抑之。
至于庶族知识分子,唐朝中央政权对其崛起是很有扶持之功的,科举取士是制度上的保证,而唐太宗提拔马周、刘、自等人,也很显出将政府官员从功臣贵族转为一般文士的企图。他的后代也有类似的态度,《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彭景直要求在祭奠山陵的礼仪上“择古作法”,受到了唐中宗的驳斥:“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显然,他对礼的态度与庶族文人相似。当然,大批地提拔进士出身的庶族知识分子,是武则天的基本国策。不过,武周革命时,因为士族子弟守礼沉正,不大肯依附诡从,而隐存李唐,所以复辟以后,清检礼法的门风又为世所重,唐政权也改变了打击政策,改为拉拢了。但庶族阶层已经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了。这样,当严格的礼学家与高谈尧舜的文士们针锋相对时,中央政权必须有强健的操纵力,一手“抑浮华”,一手“尚通脱”,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开、天盛世的景象。
安史之乱以后,强健的中央政权一失,矛盾便无法被控制,而呈互相攻击的局面。杨绾、贾至论科举,认为进士的浮薄是致乱的祸根,而李华作了一篇《质文论》,认为繁文缛礼才是无可救药的弊病,直是反唇相讥。中唐以降,士族旧门与庶族新贵已是两支分庭抗礼的政治队伍与社会力量,形成党争,而学术流别亦随此而分。
遗嘱:
自天宝以还,山东土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我殁,宜归全于滏阳先茔,正首丘之义也。
丧葬是礼的重大内容,崔氏是最著名的土族,他们不肯苟且,固是为坚持礼法清检的门风,却也是士族中根深蒂固的一般观念之体现。因而,土族肯移贯京兆、改葬京畿,除了耻与藩镇胡化同风的消极原因外,还应有积极的动因驱使他们这样做。白居易草制《答卢虔<谢赐男从史德政碑文并移贯属京兆表>》,因卢氏“昨又请移乡贯,愿隶京邑”,便赞扬道:“虽清望标门,崇冠山东之族,而丹心恋阙,耻为关外之人。”以为他要求移贯,可见“臣节逾彰”,951输诚之表示。这一类制诰,固多虚美客套,但也可以观察当时的一种观念:认为士族移贯、改葬,是向中央政权表忠,要和它死生与共。这是山东士族对唐朝中央政权的积极主动的认同。士族是正统的礼乐文化的抱持者,以此与皇权合一,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李德裕便是这
种政治、文化势力的代表。宋人于牛李党争,都认李是正面角色,就是因为他身上体现着正统儒家礼教与皇权的合一,而这正是宋人所要建设的“政教之大本”。
总之,无论士族、庶族,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也都要复兴儒学。这样,就必须在尧舜之道与周礼之间,获得理论上的贯通,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系列先圣中,找出一脉相承的精神,而表述为“道统沦”这样的形态。韩愈志在领导整个儒学复古运动,他就必须在与啖、柳学派的切磋争辩中,完成尧舜之道与周公之制的理论上的统一,这是历史的使命。
3.韩愈论“仁”的独创性
那么什么是“仁义”呢?《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后来清代的阮元在《<论语)论仁论》里就根据这一条,把“仁”解释为“相人偶”;他又检出了《仪礼》注文中的几条“相人耦”语例,判断道:“古所谓人耦,犹言尔我亲爱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这个说法影响颇广,被视为汉学的一大成绩。但细勘郑注之意,是说“人也”的“人”字与“相人偶”的“人”字音义一致,并未说“人也”就是“相人偶”之意。这里很可能是古代汉语中四声别义的问题,即此“人”字可能与一般作名词的“人”字声调有别,因为它在这里要当动词用。韩愈《原道》里有一句“人其人”,前一个“人”字也是这个用法,而“人其人”,在我看来,也就是“人也”的最精当的解释,相比之下,“相人偶”或“以人意相存问”都显得笨拙。章太炎先生《旭书》重订本《订文》篇附《正名杂义》中,有一条证明“人、儿、夷、仌、仁、*六字,于古特一字一言”,这是文字训诂方面的成果,对我们理解“仁者人也”的意思也甚有帮助。这个“人”既作动词用,为“人其人”之义,那么“仁”也便是“做人”的意思,对于自己,要努力克尽做人的职责,对于别人,要以人道的态度去对待,把人当人看。因此,韩愈释“仁”,谓“博爱之谓仁”,这个解释,比阮元的说法要深入一些,它超越了人与人之间具体的“尔我亲爱”,而触及了人“类”的爱,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当然,与这种人类的爱相伴随,还必须有“义”的规范,《史记·乐书》;“仁以爱之,义以正之。”故韩愈又谓“行而宜之之谓义”,通过“义”而与礼教相联系,正如《中庸》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因此,总“仁义”而言之,也就是《诗大序》讲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意思。
不过,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儒家虽然论证了“仁”就是“人也”之义,但接下去就不再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论述“使人是人”之类的问题,而是立即转换方向,从“人也”中直接引申出一套伦理观念,即所谓的“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儒家看来,“做人”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难题,它的内容是如此地具体易明,克尽伦常便是。韩愈也是这个思路,《原道》云:“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虽然不越出传统的思路,但韩愈仍表现出了传统学者论述伦常问题时非常罕见的独创性,即把“五常”改成了六个,原先的“朋友”一伦,这里易为“师友”和“宾主”。无须深文周纳,我们读《原道》至此,便不得不联想到韩愈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师说》。在这篇名文里,他给“师”下了“传道、受业、解惑”的定义。与程朱理学把“道”解为“天理”不同,也与陆王心学把“道”的命脉系之于“心”异趣,当然也与柳宗元、二苏之释“道”为自然相背,韩愈的“道”,是靠着“师”来传授的,师在道在,师亡道亡,根本地说,真正赐予人类以真理的,并不是“天”,而是人类当中的“师”。因此,“尊师”与“重道”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孔子以后,我国教育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笔。宋代王十朋《梅溪前集》卷十四《策问》之十六,曾指责韩愈的道统论,说:“夫道在天下,亘万世常自若也。自尧未传之前,其道如何?自轲失传之后,其道又如何?”实则,韩愈的“道”不是那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理,不是出于天赋,而是来自师授。正因为它来自师授,才能保证它以“定名”为内容,而不仅存“虚位”;也正因为它来自师授,才会出现一个传承的统绪。因此,师道论是道统论与“定名——虚位”论之间的桥梁。
还有“宾主”一伦。“宾主”是主人和宾客的关系,与“师友”中的“友”一样,可以概括到原先的“朋友”一“常”中去。但这里突出“宾主”,显然有时代性,它主要是就唐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而言,即长官与幕僚、门客的关系,推而广之,是政府官员与天下
士子的关系。可能是切身感受比较强烈的原因,韩愈要特别指出,此种关系须合于仁义之道。他年轻时,曾经三次上书宰相告饥寒,渴求汲引。后人读其书,颇以乞怜权贵讥之。那么怎么办呢?程子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饿死就饿死吧!然而韩愈的“道”却不是这种饿死道,他在《原道》中为君、臣、民各自规定了职责,而又以“宾主”一伦与之相配,倒不如小说《金云翘传》的作者有见地,其第七回首云:“韩愈饥寒,上书告宰相,人多笑之。不知此正韩愈以父母待君相也,故不惭不疑而上书。”语似曲辩,但仍有道理,因为按照韩愈的理论,他自有权力以儒家的宰相之道来要求时相,因为他的“道”本非区区的饿死道,而是要以仁义之“定名”来规范那些实施礼乐刑政的官员。所以,三上宰相书的动机虽不得知,但此行并未违反他自己的学说,他没有为此而羞愧的理由,李汉编韩集时,当然也不会把这三封书信删去。更何况,在唐人的文集中,类似的干谒性文字比比皆是,唐代士人本不以此为可耻。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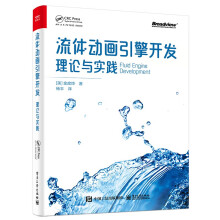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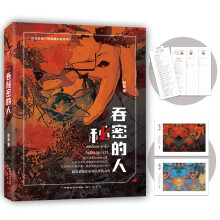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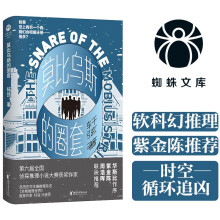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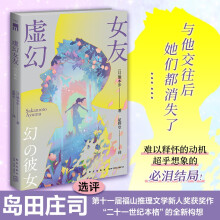

韩、柳、欧、苏,古称文章四大家,在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尤见精博。考四家之并称,来历甚早,苏轼刚刚去世时,米芾作《苏东坡輓诗五首》,其三有句曰:“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这里还缺一个“柳”。至南宋初年,苏文盛行,四家之称便随之而出,王十朋《读苏文》三条:“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杂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皆以韩、柳、欧、苏四家为唐宋文章之代表,一再标榜。《读苏文》三条,依作者自署的年月,作于“绍兴庚午七月”,即公元1150年,距苏轼去世(1101年)刚好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或已有过四家并称的文字,笔者还未能检出。故目前为止,我暂把“四家”之称的发明权归于王十朋。稍后,有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至南宋的后期,四家并称似已较为常见,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天集卷五,及李涂《文章精义》中都曾提到。到了元代,唐宋四家的说法便作为对前朝文学史的总结而确定下来,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唐之文则称韩柳,宋之文则称欧苏。”此后的材料就引不胜引了。这是对“四家”并称的历史回顾。从王十朋的文字可见,其标榜“四家”,目的在于肯定苏轼的历史地位,因此,米芾的那两句诗,虽然少个“柳”,却已经具备了这个意思。
之所以要提到米芾这两句诗,是因为它非常明确地把“文”与“道”联合起来,揭示出时人把苏轼看作韩愈、欧阳修之继承人的原因,从而也揭示出:在何种意义上,“四家”得以并称。“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可视为“互文相足”。韩愈以一篇《原道》,奠定了他作
为儒学复古运动与古文运动之双重领袖的身份;柳宗元是与他并称的同志;欧阳修在生前即以韩愈的继述人自居,且被世人所承认,他并且以“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来训励苏轼,苏轼受训,当即“又拜稽首”,表示“有死无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可见,文章四大家间亦以“道”相联结。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
但四家的成就还不止于此。文学史上所谓“以文为涛”,作为与“宋诗”之形成密切相关的创作风气,大致亦以韩愈为始,欧阳修为继,苏轼为高峰;至于词,欧阳修是宋初小令的代表作家之一,苏轼则以“以诗为词”开倡豪放派。因此,在这四家的身上,从“道”出发,通过“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将时代的思潮与各体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以同一节奏律动的文化景观。
本书旨在阐述“道”与各体文学间的深刻的联系,认为,没有“道”的宏扬,便不会有上述那些文学运动,“道”对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各体文学(尤其是正统诗文)的影响,其积极促动的方面要远远胜过消极制约的方面。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认为它可以脱离其余的文化门类而独自发展,更不认为那些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成就的作品,会隔离在当代的思想潮流之外。因此,作为一个历史的命题,“文以载道”并不能轻易否定。只要我们不是从某一家文学概论出发,而是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形出发来看问题,我们便不会在赞赏四家之“文”的同时闭目不见支撑着其“文”的“道”。如果说四家之间,后者比前者有所发展、进步的话,我也并不同意那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正。确”地处理了“文”道”关系。这种观点意味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史,是把“道”一步步赶出文学的历史。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古文运动。我眼里的四大家,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人,他们不是空头文学家,而是一身兼为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巨匠,在哲学、文艺、政治上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他们在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决不会互相否定或异辙。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上。因此我想证明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两个进展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体风貌。当然,这一致性本身还有更深的原因,植根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