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因此对现代性持一种敌对的立场,这正是福柯作品中最突出的后现代特征之一。一般而言,后现代理论都拒斥将理性与自由相等同的现代观点,并试图将现代理性形式说成是还原性和压迫性的。在他70年代的系谱学著作中,福柯指责现代理性、制度和主体性形式是统治的根源或统治的建构物。现代理性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们是推动进步和解放的力量,而福柯却将它们视为权力和统治的基本成分。后现代理论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理论模式,把它视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神话,是还原论的,它遮蔽了社会领域
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在政治上导致了对多元性、多样性和个体性的压制,并助长了顺从性和同质性。
与现代观点截然相反,后现代主义者肯定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差异性和片断性,视它们为压迫性的现代理论形式与现代理性的解毒剂。例如,福柯就曾赞扬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在实践意义上,比起“整体性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压制性后果”,“非连续的、具体的、局部的批判具有惊人的效力”。尽管他承认诸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这种整体性理论“为局部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工具”(Foucault,1980a:81),但他相信,它们在实践意义上是还原主义的和压迫性的,需要用多元的知识形式和微观分析来替代。因此,福柯试图使作为统一整体的、由一个中心、本质或终极目的统御着的历史与社会非总体化,并使主体(在福柯看来,主体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构造力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被构成的意识)非中心化。他把历史看作是由不相关的知识组成的非进化的、支离破碎的领域,把社会看作是由处于非均衡发展水平上的各种话语构成的离散的规则体系,把现代主体看作是对牢狱社会之运转不可或缺的人本主义虚构,这种牢狱社会处处对它的臣民施以规戒和限制,使其从事苦役并服从统治。
或许,福柯著作深层的主导动机就是要“尊重……差异”(Foucault,1973b:xii)。这种动机影响了他的历史学方法、社会观点以及政治立场,并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意图抓住话语的特殊性和不连续性的历史学方法;对弥漫于多重的社会场域中的权力的反思;把“普世知识分子”(general iulintellectual)重新界定为“特定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以及对整体性和总体化思维模式的批判等等。福柯从多种视角来观察现代话语和现代制度,由此来分析现代性。按照尼采的理解,视角主义(peIespectivism)否认有事实存在,坚持存在的只是对世界的解释。既然世界没有单一的意义,而是有无数的意义,因而,视角主义便追求对现象的多元解释,并坚持认为“解释世界的方法是不受任何限制的”(Nietzsche,1967:326)。例如,尼采对价值之起源的反思就是从心理学、生理学、历史学、哲学及语言学等多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尼采来说,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观察世界或其任何现象的视角越多,他的解释就将越丰富越深刻。
像尼采那样,福柯反对那种试图在某一种哲学体系内或从某一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核心观点出发系统地掌握所有现实的哲学学虚妄。福柯相信,“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Foucault.1973b:XlV)。没有哪一种单一的理论或解释方法可以凭其本身抓住构成现代社会的多元话语、制度及权力模式。因此,尽管福柯深受诸如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观点的影响,但他拒斥任何单一的分析框架,而是从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和性等多种视角来分析现代性,所有这些视角都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交错,从而提供了观察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之性质的不同角度。
(1)考古学与非连续性
福柯在其早期著作中把自己的立场称为知识考古学。他采用考古学这个术语,其目的首先是想把他的历史学方法同那种追求隐藏在话语后面的深层真理或寻求阐释主体意义图式的解释学方法区别开来。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表层一深层(Surface—depth)式和因果模式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并非由因果纽带联系来的话语的非连续表层的后现代描述。“从事怀疑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0{sUSplCion)身成了怀疑的对象。考古学同时也区别于那种“混乱的、缺乏结构(under-sTructure)或结构错误的(ill-structured)观念史领域”(Fouc:auIt,1975a:195)。福柯反对那种从传统或主体的意识产品中追溯思想之连续演化史的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写作模式。
与这种作法不同,考古学试图弄清知识的可能条件,以及使推论性理性(disetlrslgre ratl)nality)得以形成的决定性规则(这些规则隐藏在意识层面或主题内容之下发挥着作用)。“这些形构规则(rules of formari’on)正是我想要努力揭示的。尽管它们从未凭其自身资格被系统地阐述过,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广泛不同的理论、概念以及研究对象中发现它们。我可以通过隔离(is01atmg)的办法来揭示出它们的具体所在,我把这种级别上的所在称为……考古学的所在(Foucault,1973b,xi)。”和结构主义不同(尽管福柯的早期分析同结构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参见dreyfusand rabinow,1982),这些规则并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特性,也不是以心灵结构为基础,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并且随着推论领域的不同而不同。这种规则构成了所有知识、感觉和真理的“先验历史条件”(hisorical a priori)。它们是“文化的最基本符码”,构成了“认知”(eptsteme)或知识的框架,决定着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方式。
例如,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civilization)(Foueault,1973a)中,福柯就试图写出疯狂被历史地建构为理性之对立物的“沉默的考古学”(th(,archae010gv。fthat silence)。福柯回顾了以1656年的大规模监禁为标志的那次历史断裂,从那时起,现代理性中断了与疯狂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排外性话语和禁制性制度来“防备非理智行为(unreason)的潜在危险”(Foucault,1973a:84)。古典话语与现代话语建构了理智与疯狂、正常与反常的对立,由此强化了理性和真理的规范。在他的接下来名为《诊所的诞生》、副标题为“医学观念的考古学”(The Birth of the Clinic:An Archae010gy ofMedical Perception)(F0ucault,1975a)一书中,福柯分析了从以猜想为基础的前现代医学向以经验为基础的、扎根于科学探索理性的现代医学的转变过程。他拒斥那种以“临床医生的意识”(consc’IOUsness 0f cliniclans)为基础的历史,寻求对话语的结构性研究,借此来弄清“现时代医学经验的可能条件”(Foucault,1975a:p XIX)以及关于个体的科学话语最先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
紧接着,在《词与物》(The c)rdet of Things.)、副标题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FOH(、ault,1973b)一书中,福柯描述了人文科学的诞生过程。通过对生命科学、劳动及语言的变迁历程的考察,福柯详细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内在规则、假设及规范程序(ordering procedures)。在这种分析中,福柯揭示了“人”作为推论性建构物的诞生过程。“人”,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学等)的哲学对象,出现于当古典的再现领域消解的时候,也就是当人类首次变成了不再仅仅是一个冷漠的再现主体,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的研究对象,一个有限的、被历史地决定了的、被从它的生命、劳动和语言技能等方面加以研究的存在物的时候。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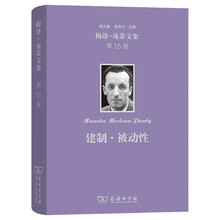
该书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严谨的态度,其二是信息量大。
所谓严谨的态度,一如书的副标题“批判性的质疑”所昭示的那样,就是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这一点说起来平淡无奇,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众所周知,对待后现代主义这一20世纪末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性文化思潮,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盲目地全身心拥护,不加分析;一种是专断地嗤之以鼻,拿起来就骂。这两种貌似截然对立的态度实则为一,都是一种思想懒汉的态度。《后现代理论》一书的作者则舍弃了这条便利异常的路,而踏上了一条远为艰难的路,一条思想之路。在书的第一章结尾处,作者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去阐述和理解后现代理论,把它看作是对现代理论与现代政治的一种挑战,既包含着很有希望的新观点,同时也有值得怀疑的向度。”又说:“我们既不当后现代话语的辩护士和颂扬者,也不会对之仅抱以轻蔑和鄙夷,相反地,我们将敞开胸怀,既接受它的挑战与批判,同时对它的某些夸大和表达方式提出质疑。”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作者不同意仅仅将后现代主义等同于一种“时尚”,而是花了相当的篇幅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得以产生和风行的现实依据。作者的考察表明,后现代 主义在政治上是对西方60年代激进政治运动失败的反应。此外,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一日益复杂的世界,传统的一套认识模式与范畴越来越显出了它的局限性。人们呼唤着新的理论、新的价值观的产生。后现代理论便是应这个“运”而生的。如果说在后现代主义刚刚兴起的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一词还是“离经叛道”的代名词的话,那么今天,诚如作者所言,许多社会、文化领域都已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客观上就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以及政治等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参见本书第41页)。其结果就是“后现代不仅已经介入我们所能设想的从人类学到企业管理到政治到科学的每一个领域”,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后现代总统制”、“后现代爱情”、“后现代心灵”、“后现代神学”、“后现代电视节目”等一系列当代大众文化的各种不同主题之中(参见本书第36页)。
面对这样一股扑面而来的思想大潮,作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学者的冷静与激情。
他们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后”(post)这个字样所包含的表示某种旧事物终结的否定性的含义,同时也应该对它所包含的另一种启示录式的含义——新东西的诞生——引起注意。
受惠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者在书中始终拒绝偏执与独断,尊重多元与差异。
也正因如此,作者对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表赞同。针对资本主义对人休的麻醉化、机械化、德勒兹和加截利强调人的创造性,强调与那些要求僵硬的中心性、权威、稳定性以及顺从性的人格类型进行对抗的重要性,因为这种主体不能忍受他人的差异并且很容易走向法西斯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