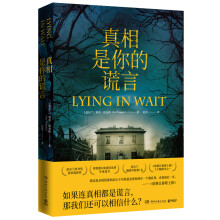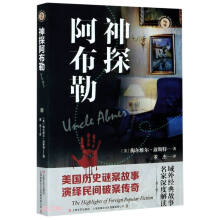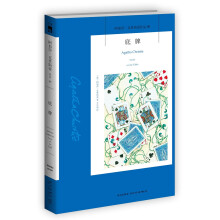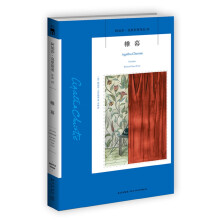1999年是德国大文豪歌德诞生250周年的“整日子”,德国是不消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纪念活动,我们中国也搞了相当规模的纪念活动,歌德作品的若干中译本也隆重再版。<br> 我想问一声:是哪位中国翻译家,率先将Goethe译为“歌德”的?为什么不采用“哥德”或“戈德”的译法?我们都知道,西欧有一种古典建筑,我们通译为“哥特式建筑”,而不是“歌德式建筑”,其实那发音很接近。<br> 因为是译作“歌德”,所以有位年轻人跑来问我:“这位德国老前辈作家是不是特别地会歌功颂德?”我不是研究歌德的专家,而且连汉译的歌德作品也读得不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br> 但我大体上知道,这位歌德老前辈,他的命特别的好。他出生在小康以上的家庭。1984年,我曾到当时的西德访问,在法兰克福参观过他的故居,那座建筑物及其庭院或许难称豪宅,但也相当地宽敞幽雅,记得我还在其花园中的小喷水池前拍过“到此一游”照。歌德十几岁就离家到德国东部上学。那似乎并非是因为家道中落,他从小就没受过苦,而且后来的社会地位与物质生活堪称“芝麻开花节节高”,二十多岁后,他成为魏玛公国的官员,后来更荣登相当于大臣的位置。他一生顺顺遂遂,国君(魏玛公爵)、同僚以及民众似乎都没怎么难为过他。他极有艳福,养尊处优,以83岁的高寿而终,被隆重地埋葬在魏玛。<br> 中国有句古话,叫“文章憎命达”,似已成为了一条不容颠簸的“公理”,但“命达”的歌德却偏写出了流传于全世界的浩荡文章,这真令人羡慕,甚至嫉妒。<br> 歌德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著有等身的诗歌、小说、剧本、散文、文艺理论,而且他还是画家、剧院经理、新闻记者、教育家和自然哲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人类匝史上有数的、可以说是得以尽兴释放出了全部才华的大文豪。<br> 中国还有句古话,叫“魑魅喜人过”,我理解这里所说的“魑魅”并非什么具体的魔鬼,丽是所谓“险恶的人心”。中国古诗里还有“身后是非谁管得”的说法。事实也确实如此。有的人尽管生前备极荣耀,死后却引出争议,甚至被人诟病,乃至唾弃——倘仅是被淡忘,那还算较幸运者。<br> 歌德呢?似乎连“魑魅”也不怎么挑他的过错。对他,人类基本上都是一直在说好话,起码是好话居多。对他的评价,从来很高,至今不见掉价。<br> 当然,“歌德”么,这个译名的用意,我想至少潜意识里,是将他定位于“御用文人”了。他确实是一位魏玛朝廷里的御用文人。凡“御用”必糟糕么?未必,像我们中国唐朝的李白,他被“御用”时所写出的《清平调》词三首,难道不是至美的绝唱么?歌德的鸿篇巨制《浮士德》就完成在“御用”期里,但他这部伟著并不“颂圣”,而是深刻地探索了人性的奥秘。<br> 影片《大地》力求写实,通片用的都是中国音乐。影片中王龙一家的曲折命运,主要人物自然率真、感情诚挚的表演,都给美国公众提供了丰富的中国农民形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他们昔日对中国人笼统而模糊的认识。影片所展示的中国农民的坚毅、勤劳,在天灾面前的无畏,以及在道德方面的分辨力给当时的美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br> 《大地》堪称是好莱坞电影中一部表现人性美的杰作。它的可贵处,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非西方民族和人民的真实可信的形象,而且在于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种族、族裔和文化的差异,来表现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人类的意志与情感。<br> 但是,赛珍珠的小说及电影也在无意中制造了新的刻板形象,那就是底层中国大众的艰辛。他们始终挣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用原始的生存手段延续生命,土地是他们唯一的生命圈。<br> 赛珍珠始终选取中国底层大众的命运沉浮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这中间不乏女作家对中国农民深深的同情与热爱,但同时也渗透着她从家庭获得的强烈的传教士心态。在美国公众看来,在遥远的东方大地上与土地相依为命的中国普通百姓,始终是需要保护和拯救的对象。这很自然地会引导他们以救世主身份自居,饱含怜悯地看待这些在宗教信仰上未开化的人们。观看镜头只对准活动在前现代原始落后环境中的底层人的电影,也同样容易引导观众将其与统治他们的政府作尖锐对立。<br> 事实上,赛珍珠的小说及后来改编的电影成为之后美国人想象共产党治下中国百姓生存状况的重要资源。<br> 关于《大地}另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的表演。露伊丝·雷娜的表演虽然非常出色,但这位西方演员显然有刻意表现中国女子逆来顺受、温顺驯良的倾向。将东方女子刻板化为低眉颌首、受尽欺凌而不知反抗的受难者形象,一直是西方人对东方女.子的主导想象。我们在阿兰这位角色身上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br> 但《大地》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票房上,都是一个成功。<br> 借着这种成功,好莱坞曾将赛珍珠的其他小说陆续搬上银幕,如制于1944年的《龙种》(Dragon Seed)等。影片《大地》拍摄之前,好莱坞曾与中国政府接触,征求拍片意见。当时的中国政府希望影片的主角能由华人出演,但可惜的是,好莱坞最终未能答应这个要求。<br> 赛珍珠的中国系列小说在当时的美国是一个文化时尚。<br> 《大地》公演期间恰值中日战争,大量关于日军在华暴行,如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纷纷传回美国,激起美国人对侵略者的义愤和对反侵略者的同情。<br> 随后,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可以说,当时的政治氛围,是像《大地》这样的电影所以流行的重要原因。<br> 海明威的魅力在于,他净化了当时的文风,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也因此,他被同时代及后来的许多作家奉为典范,并且吸引了世界上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目光。其春风化雨般的影响,经久不衰。<br> 我的书橱中,排列着有关海明威的书,其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作家。《海明威文集》、《海明威短篇小说》、《海明威研究》、《海明威与海》等等。难怪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说:这位海叔叔的书可真多,他是不是讲海的故事呀?!<br> 川人魏志远,一到上海即下海,可显著的收获却是翻译了海明威的长篇《获而一无所获》。书中写了硬汉哈里。这是海明威极富冒险精神的一次创作。译书出版了,魏志远将样书第一个送我,且在我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他知道我崇拜海明威,和他一样地崇拜。<br> 近读介绍海明威生平的一份译稿。看他魁梧、结实、胡须丛生的照片,嘴角还漾出一丝微笑。看他的年表,心头倏然一颤:海明威生于1899年7月21日。我恍然感悟,海明威已经百岁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br> 哦,海明威是不朽的。<br> 我想,很难再有像海明威这样的作家,他的经历与作品,让我一读再读。因为,海明威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br> 既然地球上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天堂里也不例外。<br> 加缪一定要穿一件时髦的T恤,上书“我不怕汽车撞我”,在天堂里四处游荡,放浪大笑;萨特和波伏瓦靠在自家窗口,看着加缪窃窃私笑,他们俩合开一家小酒馆,酒馆的名字叫“天堂里没有本质可言”,大卖一种叫“主义”的百年存酒,大发了一笔财。<br> 加缪在天堂里的职业是擦天堂后窗的玻璃,后窗里经常有人间的灰尘吹上来,每天早上擦干净了,到了晚上灰尘吹上来,玻璃又是毛乎乎一片,加缪的工作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擦玻璃,类似他这样的伙计还有:贝克特负责在天堂里拖地板,地板也是每天拖,每禾脏,日复一日地拖。<br> 加缪在天堂里还是个辩论高手,时常穿着他那件有名的T恤,找上帝逗乐子去,加缪质问上帝:“为什么玻璃总擦不干净?’上帝笑道:“你就希望它擦干净吗?”加缪笑道:“我当然希望它永远干净,省得我天天劳神费力。”上帝两手一摊,表示无奈的样子,加缪朝上帝瞪一个白眼,哼着歌儿离去了。<br> 贝克特不想拖地板,喝醉了酒,来找加缪闲聊。“既然地板天天拖天天脏,老子不想拖它了!”加缪呷一口咖啡,点点头,表示同情。贝克特说:“咱们每天在等待,等待着上帝老头给咱们一个奖赏,可不知道这奖赏什么时候会来,没法子,这地板却还得天天拖。”加缪说:“谁知道那老头会不会给我们啁,再说了,那玩意值多少钱?”贝克特听了加缪的教唆,有一个礼拜没有拖地板,天堂里的地板上积满了灰尘,上帝整天迎来送往的客人们有意见了。上帝面上也过不去,知道这是加缪使的坏,就来找加缪,许诺让加缪以后少擦点天堂的后窗。加缪忙说:“别,别,你不让我擦天堂的后窗,我以后真不知道干点什么别的差使了。”上帝说:<br> “那你得找贝克特说说去,让他以后勤擦地板,不然天堂的脸面真不知道搁哪里了。”加缪哈哈大笑。<br> 贝克特又开始拖天堂的地板了,这倒不是加缪的功劳,实在是他自个儿觉着没劲,不得不如此拖。再后来贝克特跟加缪商量,觉着换点花样工作着有趣,就轮流着擦起了玻璃,拖起了地板,单周贝克特拖地板,加缪擦玻璃,双周贝克特擦玻璃,加缪拖地板,两人在这样的活计中干出了乐趣,整天歌声不断,吵得天堂里整天闹哄哄的。<br> 上帝也没办法,由得两人胡闹去,天堂里就是这么个荒诞的所在,两人闹到后来,萨特跟波伏瓦嫌闹得心慌,一听到他俩唱歌,就把自个儿的窗儿关了,图个两人世界的清静。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