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蕴育出乡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乡者,故乡也,土者,也间也。吾乡吾土,是故士,是老家。数字化的今天,世界风云变幻。现代都市人于历史留下的印痕已无可言说。老村、古镇、旧宅、败祠、发黄的族谱,或可引发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思索。本系列旨在介绍中国民间传统的地域文化。以图文随记的形式,向大众传播中华本土文化之精髓,复苏久远的历史场景。为探究历史传承,反思文化变迁的人们,开辟一片传统文化的博物馆,乡土社会的史书库。亦借此呼吁,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珍视我们的历史!本系列旨在介绍中思间传统的地域文化。以图文随记的形式,向大众传播中华本土文化之精髓,复苏久远的历史场景。为探究历史传承、反思文化变迁的人们,开辟一片传统文化的博物馆,乡土社会的史书库。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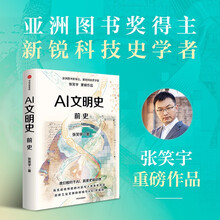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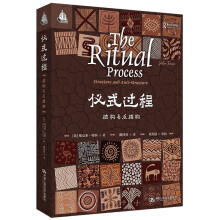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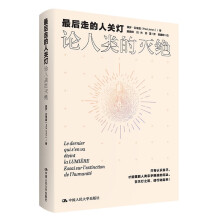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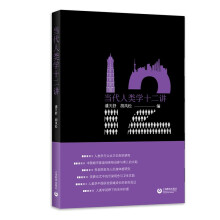
2002年岁末,12月30日。
再过一天就要过新年了。这是一个人们翘首以盼的日子。
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兴华乡摆贝村。
刚下过一场百年未遇的大雪。天空阴惨惨的,天气格外冷。远处的山脊上一片白茫茫,像画一样。摆贝村的雪虽已经融化,却仍可以看出几天前整个村寨被大雪肆意践踏过的痕迹:大树被压弯了腰,通往乡镇的山路泥泞不堪,屋檐不停地滴着化雪的水……
我坐在摆贝村寨里最受人尊敬的寨老杨写巴家的火塘前,与长者促膝而谈。老人整整70岁,一张饱经凤霜的面庞透着刚毅,皱纹深深地刻在脸上,看上去非常像我国的一幅著名的油画《父亲》。他悠悠地摆着古(“摆古”:即讲故事),那音调和节律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回音效果,构造出来的景致完全是另外一派风范:旷远而苍茫,铿锵而遒劲。
远远近近的人们喜欢叫杨写巴“苗王”,他也欣然接受人们赠予的称谓。这是一桩有意思的事情。“老”在地方上被赋予了某种权威。少数民族中的“寨老”甚至成为一个专属性称呼,它的指喻意义就是“权威”。事实上,杨写巴还不独为“老”,他在摆贝村做过几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直是党和政府在地方上的代表,是官方力量与地方知识的结合体。于是,故事便自然而然地从他的身世展:
我从18岁就开始在摆贝当干部,当了好几任的支书。1954年是组长,1958年做村长,1960年开始当支书,文革时退职,1971年又叫我到县里学习,1972年又回到村里当支书,一直到1992年。1992年我老了,退下来。2000年他们又请我当一年支书,2001年彻底退下来,就像邓小平一样,三上三下。我一点文化也没有,全凭经验办事。
他的中吻中充满着骄傲和荣耀。我纳闷:为什么人们不叫他“老村长”、“老书记”而要叫他“苗王”?甚至州、县、乡的领导下来也这么称呼。他听到外来人叫他苗王的时候总是笑着把眼眯起来。我想,大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村长”、“支书”都属于政府委任,被另外一种文化、政治和权力赋予并评价,换言之,是官方赋予并由官方来评价。“苗王”则由当地苗族自我认可和评价,是一种族群性、乡土性价值;这种价值才真正属于苗族自己,名副其实。
我还纳闷,杨写巴自己说他没有一点“文化”,凭什么能够当这么老久的“官”呢?又为什么摆事实贝地方都买他的账?而且我注意到,当他在讲自己“没有文化”的时候,那眼神中不仅没有流露出缺憾和自卑;恰恰相反,那眼神充满着骄傲和自豪。我想,“文化”在这里多半指他没读过书,不识字。这是主体民族——汉族的价值指标,即:不读书、不识字就“没文化”。我们已经相当习惯地把不识字的人叫做“文盲”。也就是说,不识字就是“瞎子”。相反,“文明”的基本指示是:识得文字,仿佛“日”“月”一般的“明”。从这个角度说,或者在汉族社会的价值系统里,杨写巴是个“文盲”。可是,在那摆贝地方的苗族中间,他却是个“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