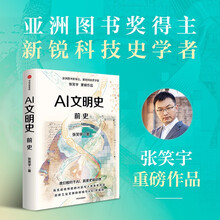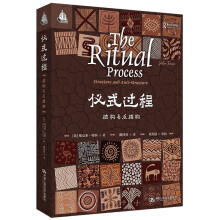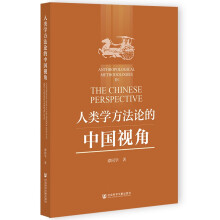人类在自身的心理思想与历史的脉络中行动。在我们身上不但存在着我们以前曾采取过的种种立场,还带有一切我们将来会采取的种种立场。我们同时存在于一切地点,我们是往前冲的群众之一,不断重现以前出现过的一切阶段。因为我们存在于一层层包裹着的世界里面,每层世界都比包含于其中的世界更真实,但又比将之包含在内的外层世界更不真实一些。有些世界能经由行动而被我们认知,有些我们只在思想中经历过。然而要如何解释不同的世界并存时在表面上显示出的矛盾呢?那是由于我们都觉得有责任为最亲近的世界赋予意义,而拒绝承认较疏远的世界有任何意义。实际上,真理存在于一步步让意义扩大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与我们的感觉正好相反,一直到意义本身涨大到爆裂为止。情形既如上述,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一样,已深深为影响到全人类的一个矛盾所困扰,这个矛盾有自身存在的内在理由。只有在把两个极端孤立起来的时候,矛盾才存在:如果引导行动的思想会导致发现意义不存在的话,那么行动又有何用?然而,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发现意义不存在――我必须经过思想过程才能得到那个结论,而且我无法一步就完成整个过程。不管整个过程是像释迦牟尼所说的有十二个步骤,还是有更多或更少的步骤,这些步骤均同时存在。为了得到上述结论,我便要不停地生活在各种不同的情境里面,而每一种情境都对我有所要求:我对其他人类负有责任,正如我对知识负有责任一样。历史、政治、经济世界、社会世界、物理世界,包括围绕着我的一圈一环的天空,所有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无可逃避的;要在思想上脱离它们,就不得不把我自身的一部分割让给它们中的每一个。像一块击中水面形成一圈圈涟漪的圆石一样,为了到达水底,我不得不跳入水中。当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当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我将用一生去设法了解、描述的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烟花,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些烟花不具任何意义;即使有意义,也只不过是整个世界在它的生灭过程中,允许人类去扮演人类所能扮演的那个角色罢了。然而人类的角色并没有使人类具有一个独立于整个衰败过程之外的特殊地位,人类的一切作为,即使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并没有能力扭转全宇宙性的衰亡程序。相反,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过程里最强有力的催化剂,急速地促使愈来愈强有力的事物进入惰性状态――一种有一天将会导致终极的惰性状态。从人类开始呼吸、开始进食的时候起,经过发现火和使用火,一直到目前原子与热核的装置被发明出来为止,除了生儿育女以外,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过是不断地破坏数以亿万计的结构,把那些结构肢解分裂到无法重新整合的地步。没错,人类建造城镇、垦殖土地。然而,仔细想想,我们会发现城市化与农业本身就是创造惰性的工具,城市化与农业所引导创造出的种种组织,其速度与规模远比不上两者所导致的惰性与静止不动。至于人类心灵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其意义只有在人类心灵还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一旦人类心灵本身消失,便会陷入普遍性的混乱、混沌里。因此,将整个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的话,可以说它是一种异常繁复的架构和过程,其功用如果不是为了创造、产生物理学家称之为熵(entropy),也就是惰性这种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很想认为它给人类世界提供了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每一句对话,每一句印出来的文字,都使人与人之间得以沟通,沟通的结果就是创造出平等的层次。而在得以沟通以前,有信息隔阂存在,因为隔阂的存在而同时存在着较大程度的组织性。人类学实际上可以改称“熵类学”(entropology),改为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然而我存在。我当然不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存在的,因为就这方面而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赌注与战场,一个永远处于危险之中的赌注与战场;只不过是一个由我脑壳中数以亿万计的神经细胞所组成的社会,与我的身体这具机械两者之间斗争的赌注与战场。心理学、形而上学和艺术都无法给我提供任何庇护所,那些全都是神话,只是一种即将出现的新社会学的研究标的,这种新社会学处理以上种种神话的方式不会比传统社会学更客气。自我不仅仅可厌:在“我们”与“空无”之间,根本没有自我得以容身的处所。如果我在最后选择了“我们”(us)的话――虽然这个“我们”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的雷同――那么我还是会投入其中,其理由不外是,除非我毁灭我自己――这样做就不用再做选择了――否则我在表象的雷同与空无之间只能做一选择。我只能有一种选择,这选择代表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人类的处境,使我从知识的傲慢之中解脱出来。知识的傲慢毫无用处,这一点我可由其目标的毫无结果看出来。在做出选择的同时,我就会同意顺从于可以让大多数人获得解放的种种真实需求,而他们连做出选择的机会都无法获得。就像个人并非单独存在于群体里面一样,就像一个社会并非单独存在于其他社会之中一样,人类并不是单独存在于宇宙之中的。当有一天人类所有文化所形成的光谱或彩虹终于被我们的狂热推入一片空无之中时,只要我们仍然存在,只要世界仍然存在,那条纤细的弧形,那条使我们与无法达致之点联系起来的弧形就会存在,就会向我们展示一条远离奴役的道路。人类或许无法遵循那条道路前行,但光是思考那条道路,就会使人类获得特权,就会使自身的存在有了价值。至于中止整个过程本身,控制那些驱动力―那些逼迫人类把需要之墙的裂缝一块块地堵塞起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牢笼里面,耽溺于自己的工作成绩的驱动力―这是每个社会都想取得的特权,不论其信仰是什么,不论其政治体系如何,也不论其文明程度高低,每个社会都把它的闲暇、它的快乐、它的心安自得以及它的自由与这种特权联系在一起。这种对生命来说不可或缺的、可以解开联系的可能性(哦!对野蛮人说声亲爱的再见了,告别探险!)就是去掌握住,在我们人类这个种属可以暂时脱离如蚂蚁般庸碌重复的活动时――在思想的世界之中、在社会的界限之外――想一想存在以及继续存在的意义:对着一块远比任何人类创造物更美丽的石头沉思一会儿;闻闻水仙花深处散发出来的味道,这香味里隐藏的学问比我们的所有书本的学问加起来还要多;或者是并非刻意为了了解对方,而仅仅是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地短暂凝视对方――有时候,一个人与一只猫对望,就像那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