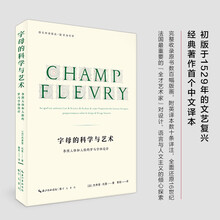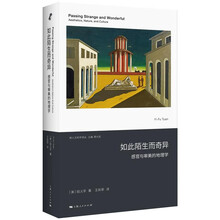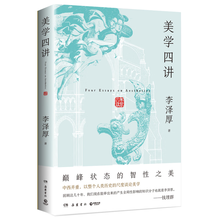在如何创建中国现代戏剧的问题上,似乎存在着两种观念,两条思路。如果说,汪仲贤、陈大悲、蒲伯英等“为人生”论派偏重于追求戏剧的社会功利的话,那么宋春舫、余上沅等“纯艺术”论派,则更倾心于戏剧的艺术形式与民族审美心理的雕镂和探究。
“为人生”论派从《华伦夫人之职业》演出失败的教训中,悟到了戏剧适应国情和民族审美心理的重要性,而宋春舫却从这次外国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的败绩中,进一步认清了戏剧的艺术本质:“戏剧是艺术的而非主义的,”他认为,戏剧并不是靠什么“主义”或“人生观”去吸引观众的,而是靠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去点燃拨动人们的审美心理与欣赏情趣。在他看来,《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之所以失败,就因为“问题派剧”的倡导者,只在宣传“主义”,并没有认识到要“迎合社会之心理”这一戏剧艺术的“唯一之目的”,因此,他主张放弃易卜生式的“陈义高尚”,令人难以索解的“问题剧”,而取法专重戏剧“构造”与艺术技巧的法国“善构剧”等,借以创造中国的未来戏剧。显然,与“为人生”论派重社会功利相反,宋春舫试图开辟一条超功利、重形式的中国戏剧的道路,在这方面,余上沅的理论和观点更鲜明,因而也就更引人注目。
余上沅对“五四”以来,中国戏剧“归向易卜生”的“趋向”颇不以为然。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纯艺术”观点与易卜生的“问题剧”相拮抗,而是他不赞成崇拜“英雄。与“偶像”,忘了自己创造的责任。“不然,爱尔兰的剧场,让易卜生的旗帜飘扬着好了,何必又要建设爱尔兰国家剧院”呢?的确,余上沅是有创建民族新戏剧的雄心和胆略的。这不仅反映在他留美期间与好友闻一多、张嘉铸、熊佛西等为振兴中国戏剧,那种相互砥砺、跃跃欲试的意气与宏图上,更表现在他回国后与同道们所发动的那场“国剧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关于“国剧”的构想,他是从“纯艺术”的观念出发,却又与宋春舫心目中未来戏剧蓝图不尽相同:他主要
不以外国戏剧为。范式”,而是立足于中国旧剧“写意”的美学原则,汲取西方“写实派”的“理性”因素,以创建“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完美戏剧”。然而,超功利、重形式的艺术观念,余、宋二人却又是基本一致的。
一个重功利、轻形式;一个超功利、重形式。这是本时期在创建中国现代戏剧过程中,存在的两种互相对峙的美学倾向与思路。一般地讲,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戏剧艺术的特征与规律;伹前者更偏重戏剧的社会作用与功能,而后者则往往醉心于“超功利”的“纯艺术”的刻意讲求,二者各有优势与偏执,又各有复杂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理论渊源;前者主要受西方现实主义美学传统的启迪,后者则明显地烙印着西方形式主义美学思潮的标记,二者互相矛盾而又互相补充,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步态与走向。
其实,言语也“是动作的一种”。熊佛西似乎只看到了言语之外的动作,却尚未认识到言语本身所蕴含的动作性。这是同当时中国以至西方戏剧理论所达到的水平相一致的,20年代初,产生广泛影响的戈登·克雷关于“傀儡戏剧”的构想和理论,就相当地忽视了戏剧语言在动作上的意义。即使是贝克的《戏剧技巧》一书,基本上也没有论及言语与动作的内在联系。例如他说:戏剧的历史表明,“在各个时期里,广大观众不论有教养或是无教养的,首先爱好的是动作,然后才把性格描写和对话,作为更好地理解剧中动作的辅助而加以爱好。”因此,熊佛西这一理论上的不足,是能够理解的。
对表演艺术的见解,尤能反映熊佛西独具的眼光,按照熊氏的观点,戏剧的特有魅力与美感力量,归根结底来自人的情感、意志相激相荡而进发的生命火花。这主要是透过剧中人的“内心动作”和渗入其中的艺术家的情感,个性表现出来的,这一点,在他关于表演艺术的论述中,看得较为真切;他认为,演员在表演时,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他说:“吾人深知演员最要紧的使命是摹仿。摹仿不难。亲切的摹仿则难,则非艺术家不可。亲切的摹仿芷是演员自由发挥的结果。画家心目中的自然与想象,正如演员的剧中人的个性。”这里所谓“摹仿”,是指演员对剧中人的“内心动作。的摹仿。“亲切的摹仿”,是“灌入艺术家生命”的“内心动作”的摹仿,即演员想象中的“剧中人的个性”的摹仿,他认为,演员之所以被称为艺术家,就在于“亲切的摹仿”中燃烧着艺术家独特的情感与个性。正是在这一点上,熊佛西与戈登·克雷的表演理论产生了分歧。戈氏排斥和否定演员在舞台表演中把自身的情感与个性融入剧中人的性格之中,而仅仅将其看作是:“忠于”剧本的被动的、机械的“木偶”,因而否认演员是艺术家。与戈登·克雷相反,熊佛西则“承认演员是艺术家,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他与诗人、音乐家、画家、雕刻家有同等的地位,可以自由发挥他的“思想及种种美的表显(现)的风味与格式”。“戈登·格雷所谓演员不能自由发挥其个性者,吾正谓其所以成为艺术者在此。”可见,作者重视表现人的情感、意志,尤其强调艺术家的主体生命意识与独特个性的“灌入”,并将其视为表演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表现”的美学因素。
尽管如此,熊佛西仍然从戈登·克雷趋于极端的理论中看到了某些合理的因素;他否定演员独特的情感与个性,而提出“傀儡戏剧”的设想,乃是立足于戏剧是“动作的摹仿。这一戏剧艺术的根本原理的。对此熊氏说:“戏剧的起源本是始于动作。所以哑剧在古代就很发达。如今在欧美还是很流行,我想戈登·格雷主张的傀儡戏,难免不脱胎于此。”
但是,总的说来,熊佛西的戏剧美学大厦,还是建筑在以亚里斯多德“摹仿真”说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对戏剧本体、表演艺术和其他戏剧因素的探讨,就总是以“动作的摹仿”这一基本观念为出发点或与之联系、呼应的。即使在他强调演员即艺术家主体情感、个性的“灌注”在戏剧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时,也还是以对“剧中人”动作的摹仿作为不可超越的前提条件。所谓“亲切的摹仿”,就是主体(艺术家)的情感、个性通过客体(剧中人)的动作的摹仿表现出来。“再现”的美学原则,在这里依然起着决定的作用。这在作者对戏剧艺术功能的认识上,表现得就更为鲜明。
(三)
熊佛西看到了戏剧艺术的独特品格与审美肩性,但他同时注意到戏剧与人生的复杂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戏剧与“国情”、“伦理”等不可摆脱的联系的认识上,更反映在他对戏剧社会功能的揭示中。他说,“戏剧是艺术中最复杂的一种,又是与人事最有关系的一种,当然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山熊佛西认为,戏剧兼有审美与社会教育两种功能,即给人以“正当的”、“高尚的娱乐”;这种娱乐,即“负有与人愉快教训两大要素”。后来他又说:“假如你说戏剧是教育,那么教育里亦有娱乐。假如你说戏剧是娱乐,那么娱乐里亦有教育。教育与娱乐是分不开的,”总之,“寓教于乐”是他对戏剧功能的基本看法。
在这里,熊佛西还是从戏剧的独特品格出发,来论述戏剧的功能的:首先肯定戏剧是一种“娱乐”(审美),然后又说“娱乐”中含有“愉快教训两大要素”。他在论述悲剧与喜剧的社会作用时,同样坚持了这一原则。他认为悲剧和喜剧有其不同的审美创造机制与美感特征,它们的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是不能脱离这些机制与特性的。如他说,悲剧是诗类最严重最高尚的一种,其目的在使人类“恐怖”与“悲悯”的情感,得到适当的宣泄,以启发人类的同情心与敬畏心。他认为在充满了“冷气”、“阴气”、“霉气”和“乌烟瘴气”的中国,假如我们希望一点“同情之泪”和“任人生出敬畏之感”,那就应该“赶快起来提倡悲剧的艺术”!喜剧作为一种笑的艺术,惟有,“倒行逆施”、“虚伪狡诈”、“愚蠢癫狂”,才能使人发笑而成为它的创作材料,看看现实中的这些黑暗现象,“我们就可以立刻感觉喜剧对于今日中国社会的重要”。可见,熊佛西并不是单纯地、孤立地论述戏剧的社会功能,而仍然是从戏剧的本体出发,将它与戏剧审美表现的特点和途径的阐释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我们既可以认识作者观照“国情”与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又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他的“寓教于乐”的戏剧美学思想。
应该指出,“寓教于乐”是熊佛西现实主义戏剧美学思想的核心。这既与一般的“为人生”论派不尽相同,也与“纯艺术”论派有原则区别:他强调戏剧艺术的独特.品格与审美属性,又承认它的社会功能。他并不认为戏剧是所谓“超时代”、“超功利”的“纯艺术”的东西,而是真切地体察到戏剧与时代、与社会人生不可摆脱的关系,明确意识到了戏剧艺术家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他所反对的,是那种只追求社会功利而忽视艺术、甚至不顾或取消戏剧独特品格的非艺术倾向。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在20年代尤为难得。
现代喜剧观念是在20世纪初,同现代悲剧观念一起由西方引入的。在我国,最早介绍现代喜剧观念的,还是王国维。他的《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被认为是现代喜剧观念介绍与研究的开山之作。之后,从“五四”到20年代,现代喜剧观念研究同悲剧观念研究相比,显得有些滞后与薄弱。进入30年代,现代喜剧观念的研究与探讨才日趋活跃起来,足以与悲剧观念的研究互相辉映,形成了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史上耀目的一章。
西方喜剧美学的研究,如同悲剧美学的研究一样,历来存在着两种思路、两条路线:一种是从审美客体的角度对喜剧作哲学、社会学的阐述;一种是从审美主体的角度对喜剧进行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坚持前一种思想路线的代表人物有亚里斯多德、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后者的代表人物主要为柏拉图、康德、柏格森等。我国现代喜剧观念深受西方喜剧美学思潮的影响,也基本形成了与西方大致相似的两种思想路线。这在20年代已见端睨,到30年代则较为分明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