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和艺术发生关系》是《艺术世界》杂志推出的十几辑专栏文字的汇集。虽然没有前言和后记,但编者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尤其是特意安排的不同艺术领域内的顶尖人物之间的坦诚对话,更令读者获益匪浅。在《拿起镰刀,看见麦田》(王安忆VS陈丹青)中,引领我们思索个人与时代、真实与艺术的关系;在《明式家具、鸽子、蛐蛐合奏曲》(王世襄VS黄苗子)中,我们不得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本来文化艺术都是一种心灵的游戏,好玩的;但一到商品社会就变了,变得惟利是图,什么都打算盘,把好玩的东西摆在一边,不好玩了。”在《与昆曲结缘》(白先勇VS蔡正仁)中,我们能从已然式微但魅力无穷的昆曲艺术中,领略和顿悟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所在。<br> 自然,这些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文字不像正经八百的文章那么逻辑严密,讲究句法或结构,但恰恰是这些不经修饰的记录,完整地展示了思维的过程本身。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没有起承转合,不必字斟句酌,忽而说事,忽而说理,来回穿插,随意自由。即便是不曾覆盖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往往正是有意思的想法,是又一条通往思维终极的小径。甚至,对话的形式结束了,而留白处的空间却足以展开另一场新的对话。<br>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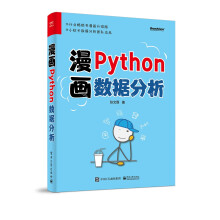






所以编辑来做一些事情了。为了防止不自觉的专业化,就让不同的专业宋面对面:画家和建筑师,作家与表演艺术家,音乐学者与舞剧编导;让两个专业领域不同的人对谈,他们的思路也许更能出新出奇,谁也不知道面对自己不太熟悉的另一门艺术,该怎样去进入。由此,他们可能会比较纯粹地在艺术感觉和艺术思维的层面上碰撞。
来搞对对碰了,看看会磋出些什么?
开首一对:阿城和登琨艳.在我们还不知道“谈话”的面目时,是他们的隆重出场.以他们五十岁已非同寻常的目光平视建筑——一个好的建筑师非得要五十岁方能成就,才将我们的谈话主题聚拢、呈现。他们俩很久前就相识,都曾周游世界,看过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许多建筑,深谙文化时代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心知肚明各种所谓新潮和守旧。他们一个西装背心名牌衬衫一个中式棉袄圆边毡帽,在登琨艳租下的1933年造的老房子(当年上海滩老大杜月笙的粮仓,改造为现代风格的建筑工作室)里,两千多平方米的空间上下两层几乎没有被间隔,在靠窗的小圆桌旁,阳光透过落地长玻璃窗照在手持烟斗的阿城身上,第一个“谈话”就这样开始了。在近千平方米的空间中,安静地喝着茶,录音机“沙沙”地转动着,建筑的无言的力量,不容忽视的尊严和不可泯灭的时代印记,就这样变成了文字。谈话发表后,有一次,登琨艳去宁波开会,来接机的人素不相识,紧握他的手背诵说:“建筑是很可怕的”。时代过去很久,它还站在那里呢。
最体现“谈话”特色的一对:王安忆和陈丹青。会明白什么叫做旗鼓相当,遇强则强,什么叫山重水复,峰回路转;在复听录音时,我还更添了一层佩服,他们的话,写下来就是一串串精彩的句子。思想是需要完美的表达的,有时候表达就是艺术。想法要靠成熟的生命去养育,如水之实体,表达却是生命的河道.其开掘修缮同样需要精力和智慧;水流之速度和形状,因地形和时段的不同而变幻,时而壮观时而旖旎。对于“谈话”而言,限时限刻的一段时空,在思想交汇的一刻,两个人都需要激光一般的速度为自己的水流开掘河道。这是很壮丽的一刻,我想,有感应的读者,是能够体会到的。
这也是“谈话”的魅力所在,有很多空泛的、虚假的陈词滥调会在这样的速度面前溃败;真知灼见容易被引导出来。如果平日思维平庸,体验匮乏,会无法承受这样面对面的交锋;一个人受激发之后会爆发更大的能量,我们也就顺着速度去网罗空气中漫散的言辞。
这在某种程度上还真是双赢。
就这样一对一对地碰了下去。感谢所有参加我们“谈话”的卓越人士,他们都是敬业而智慧的人,将长久深厚的积累薄发于短短十几个页面,使本书的内容值得反复阅读,深长思之。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