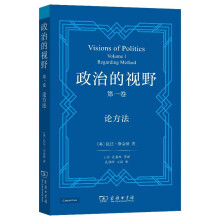虽然《基础》在这方面是脆弱的,但如果假定本书是1960年代及以后流行于历史学著作中的“现代化”论题的代表,那就误入歧途了。这个论题的倡导者们几乎都把现代早期视为“中世纪”或“传统”与现代间的尖锐的断裂。传统的政治科学对于出现于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之间并是“现代性诞生”基础的国家概念投入了大量精力,好多本科教材仍然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相反,《基础》的成就之一,就是它打破了传统的、被典型地定义为“现代之诞生”的时间界限。这本书的大部分是关于中世纪的,第一卷的标题《文艺复兴》有点模糊了这个事实。它的最早的时间是1085年。更令人吃惊的是历史重心关键性地从正统——马基雅维里、博丹、霍布斯——转到了意料不到的人物——巴托鲁斯、马西略和但丁。
在《基础》中,有大量关于罗马法和古典修辞学对时代适应的论述,不过,对中古的探讨,以及第二卷围绕路德、加尔文和反宗教改革的建构,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神学问题。可以论证的是,《基础》在严肃对待政治神学方面,是忠诚于它的历史主义指令的。这与斯金纳不时带有“现代化”命题味道的、关于世俗化起源的方法论评论有所冲突。①这也与他所谓欧洲思想中异教的、西塞罗式的潮流无所不在的观点不相一致。②而且,这也与他敌视基督教的个人喜好不相一致。③纵然如此,向基督教政治神学及中世纪的转向仍然是本书的主要部分,这种转向有着重大的后果。本书的特色部分是进一步处理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结果,不过这时斯金纳肯定是反对该命题的,因为该书打破新教与现代性间的联系。转向天主教的中世纪,他注意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传统,也是一个德国人且与韦伯同时代,一个特别与奥托·基尔克,以及英国的约翰·尼维尔·菲吉斯相联系的传统。这是一个历史理解的传统,正如即将详细考察的那样,它与剑桥大学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早根源密切相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