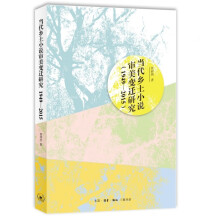雅斯贝斯掷地有声指出:“我对上帝的确定是我自身存在的力量。”①只有自由的人才仰望“上帝”;自由乃意味着人应该自由且能够去自由。人对“超越存在”或“上帝”的悬设,其人文隐衷便在于对人之为人所当承担的自由之责任作一种应然的提醒。其实,这依然是自由的人对人所当有的自由的自我提醒。在雅斯贝斯看来,“超越存在的帮助只在如下情形中向人显示它自身:人能够是他自身。他能够依靠自身而生存,他被超越存在伸出的无形的手所牵引,只有他是自由的,他才能感觉到这只手的在场。”②这句话的秘密无非在于:“超越存在”作为康德意义上的道德之元宰的“上帝”,它以其完满得无以附加的神性烛引着人的自由,而且只烛引那些心向自由且敢于去自由的人。因此,雅斯贝斯的“哲学信仰”从“生存”出发而对“超越存在”或“上帝”的悬设,已不再是实体化的信仰那样的让人匍匐于他在之命运的“神”的戒令,而是自始把诉诸自由选择的“生存”置于致思的中心,以先前“实存”对实体化了的“神”的那种眷注去眷注那总在眷注着虚灵不滞的“神性”的自由的“生存”。自由的生存出于自身的内在趣求需要“神性”的引导,这种旨在成全人的自由的引导完全不同于那种全然他在的“神”向着囿于世界之中而不再选择自身的“实存”所颁布的训令。这乃是因为,“超越存在的引导所提供的是非客观的确定性,它与人完全达致的自由相一致,并且只以主体自由的方式来运作。……在主体确信的自由中上帝的声音变得可被听见,而且这是唯一的渠道,通过它,上帝把自身的消息传递给人”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