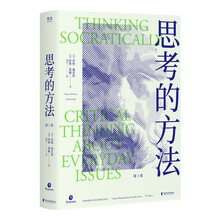第一章 超越道德、宗教之后:探索问题的新时代<br> 在《天使与章鱼》(The Angel and the Octopus)一书中,西蒙·雷斯(Simon Leys)与读者们分享了他对当代哲学著作的失望之情。作为一位饮誉世界的汉学家,雷斯对某一探讨自己所偏好之主题的作品期待已久,该书甫一面世他便购得一本。然而,几番阅读尝试以后,他终于不堪忍受书中概念注解之繁多,只好作罢。由此,雷斯描述了这种沮丧如何令他想起埃利·威赛尔创作的一则逸闻:一名犹太传教士要去附近的村庄参加一场婚礼。他雇了一辆马车载他前往,车夫也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可是刚一动身,车夫就礼貌地要求传教士下去帮忙推车,因为那匹马年迈体弱,根本拉不动车。传教士很乐于助人,便答应了。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可惜婚礼早已结束。传教士非常失望,同时他不乏机智地试图解释这一意想不到的变化,他对车夫说,“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来这儿:你需要挣钱。我也知道我为何而来:我要参加婚礼。可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带着一匹马来。”<br> 哲学作品就好比是那匹老马?这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或许你认为它只是片面之词,但此处它至少可以引导我们明确应当如何检验哲学。今天的哲学往往被简化为“论……”,简化为与其词源学语义所揭示的主旨——“对智慧的爱”——相去甚远的评注。然而当它在希腊人中间发端时,哲学其实是被视为一种与对人生态度不可分割的智力活动。它的终极关怀就是“生活”,“人应当怎样生活?”是哲学首要的问题。即便当它转向对物理学、数学或是逻辑等高深学科的探索时,其最终的目标仍是从中寻求一种能够真正为生命历程提供指引的(从字面意义上讲)“切实可行”的答案。<br> 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e Comte-Sponville)力图重建那一古老的传统,将哲学定义为“思考生活,体验思想。”这一表述不仅巧妙地首尾呼应,更清楚地说明了思考与生活两相结合的必要性。我欣然将其纳为己用,但有个前提,必须补充在我看来十分关键的一点:我们被感召着要思考的人生,以及我们采取某种哲学态度后即将体验的思想,既非日常生活也非日常所想,而是在人类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这一前提下的生活和思想。希腊人深刻地意识到,因为我们注定要死去,而且我们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将要失去那些自己亲近的人儿,因为平庸不断威胁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关于“好生活”的问题——何为此生(而非彼生)真正的价值所在——值得推究。也正因为如此,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一直都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能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伟大的哲学思想大抵与“(灵魂)救赎”有关。<br> 或许有人会反驳道,以这种方式把救赎性归因于哲学恐怕会导致哲学和神学的混淆。况且,将哲学与人类的有限性及其缺憾(厌倦、平庸、愚昧、邪恶、疾病、苦难、死亡等等)过多地联系起来,会不会又矫枉过正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对待语言、科学、道德、法律、政治以及更多其他学科?要知道它们的出现对20世纪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莫非“哲学化就是学会怎样死去”这一老掉牙的警句依然适用于当代思想,别忘了,后者可是一直前所未有地致力于“解构”形而上和宗教的幻觉呢。<br> 也许吧。但这恐怕就误解了我所指的“救赎”,此处救赎决不以任何超越现实生活的范畴——能够给予人类救赎手段的神灵们的栖息之所——的存在为前提。直截了当地说,宗教与哲学在这一方面的区别大致可以归结为:宗教做出“我们会被救赎”的承诺;哲学则恳请我们“拯救自己”。从谦卑与自豪、信仰与理性、他治与自治这几对反义词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这两种态度之间有着霄壤之别,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宗教并不能被简化为他治,现代个人主义也绝不是自治。信仰同样可以是一种自由的行为,一种深思熟虑之后对(即便出自上天的意旨,却也要留待人类来承担全部“责任”的)召唤心甘情愿的响应。就现代人的自由而言,一切都表明,受社会和历史无意识的影响,它并不排除来自于外部的决定因素。心理分析和社会学的存在本身就不断见证了这种决定因素,生物学的存在更不待言。然而,世界越是揭开它玄秘的面纱,其中栖息的神灵就越少,依靠自身努力拯救自己而非等待救世主的观念就越显得合情合理。在这一点上,从斯宾诺莎到尼采,即便是最为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也未能摒弃与“至福”(beatitude)或“永恒轮回”——简言之,与“超越”了日常生活的领域——之间的某种联系。倘若没有什么是绝对值得经历的事,那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关于“好生活”的探询?另一方面,我们怎样才能容许一种绝对的存在而不必退却到宗教的或然判断上?这就是问题所在。<br> 为了更好地界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来到我们跟前,并如同他对年迈的浮士德所做的那样,许诺让我们拥有俗世的成功可能带来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同时我们假设他会像任何名副其实的恶魔那样,要以此交换我们的“灵魂”,抑或任何我们可能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不论对错与否,譬如道德或精神信仰、政治忠诚、情感或其他依附等等。那么,当他试图夺走我们的“灵魂”时,是不是肯定不会遭遇契约中的免责条款或附加条件?我认为有可能,而且这一假设很耐人寻味。可也不一定必然如此,我知道兴许有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恶魔是不会得逞的。为什么呢?我会问,理由是什么?尽管这一命题看起来过于简单,甚至毫无价值,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对等的表述方式,但在我看来它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促使我们扪心自问:在一个彻底世俗化、权力意志压倒一切、“相对性”似乎成了全世界唯一前景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妥协”从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绝对的存在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我们在沉思好生活的时候能不能抛开这种想法?我以为不能。我甚至不能确定尼采是否相信可以将其抛诸脑后。尼采似乎认为很多事情都是“不可妥协”的,而绝不是相对抑或中立的。请允许我先做一个与此相反的假设:我们思考关于“好生活”的问题时可以完全不去理睬任何绝对的存在,无论这些存在是什么。果真如此,我们又怎能不顺从于对手段、成绩本身、那些可以估量和可以妥协之物一总而言之,对我们通常称之为“商品”之物,娱乐与消费的帝国——的狂热?!<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