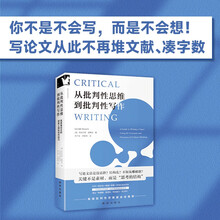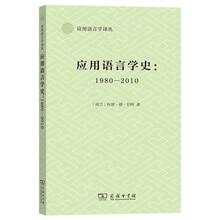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
在19世纪中国出版的外国历史著作,大部分是由外国传教士编译的,而且这些史学著作多以综合性的通史为主,但《普法战纪>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这是一部区域性的专史——一部欧洲战争史。该书的编译者王韬也是晚清早期在西学翻译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
1870年,以研究世界史地来探讨改良中国政体的著名思想家王韬。从欧洲回到香港后即撰成《法国志略》。同年八月,他根据南海人张宗良(芝轩)据英文口译的资料,参考何玉群、梅自仙等的译述润色,以及陈蔼廷在《华字日报>上刊载的有关“搜罗富有”的欧洲列国的译文和各种日报所载资料,开始了《普法战纪》一书的编译工作,次年六月“荟萃贯串,次第前后,削伪去冗,甄繁录要”,按时间先后,汇编成书。曾以抄本的形式在学界流传,颇受好评。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由中华印务局活字版排印,共14卷。后又重版,增补6卷。
《普法战纪》详细地介绍了普鲁士帝国与法国之间战争发生的原因、经过、议和与善后事宜。指出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19世纪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大战争,“欧洲全局之枢机总括于此矣。普强法弱,此欧洲变局之所由来也”。为了让中国读者对普法战争爆发的背景经过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该书采用的是寓纪传体于编年体之中的写法,不拘形式,因-事命篇,以避免“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弊,不惜篇幅详细介绍了法国七月王朝的政府首脑发孚(今译法夫尔)、爹亚(今译梯也尔)、普鲁士首相俾思麦(今译俾斯麦)、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等“矫矫不群者”的事迹。记录了欧洲政治制度及其实施情况,各国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最新军事武器和战术的运用,飞天球、空中摄影、军用地图、电报铁路等等,风土人情也点缀于叙事过程之中,写得栩栩如生。王韬对普法战争时的欧洲形势作了介绍和估量的同时,着重分析了法败普胜的原因,首先指出了人才是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的关键,“有国家者得人则兴,失人则亡;得人则弱可以为强,小可以为大。”普鲁士的国土还不及粤东二三省来得大,人口也谈不上繁盛,但由于普鲁士政府能够得人用人,终于转弱为强,成为欧洲的霸主。其次,他强调了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书中对普鲁士采用“发火极迅而绝少渣滓”的新式火药,360度旋转“可纳弹三十七枚”的“墨迭而鲁士炮”、“腾气载人”的“侦察飞球”、“一触即发”的新式枪支,乃至描绘精确的军用地图都有详细的介绍。他认为不打无准备之战,只有在人力、武器方面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法之所以蹶。普之所以兴者,无他,在有备与无备而已”。第三,他认为武器的精良固然重要,但交战双方不仅仅是装备的角力,也是两国制度优劣、民心向背的一个反映。普鲁士“议会君主制”(即君主立宪制)要比当时的法国君主专制来得优越。并详细地区分了“君为主”、“民为主”和“君民共为主”这三类政体。显然,王韬的这些史论是有的放矢的,他希望中国读者读了这本欧洲战争史能够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是中国人编译的历史著作中首次记录和分析了巴黎公社起义的史实,在卷六中描述了1870年10月31日巴黎工人和一部分国民军推翻国防政府的起义,卷十二记述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和梯也尔对公社的镇压。王韬最后评价道:“法京乱党自始事以迄卒事,被戮于官军者数十万,妇女、童稚皆不得免。”他认为巴黎公社起义的原因就是“自主”二宇。虽然,王韬在该书中有关巴黎公社的记述和分析,反映出当时中国士大夫对于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解。《普法战纪》还第一次译出了著名的《马赛曲》,题名《麦须儿诗》,共译出了四段,其中第一段的译文是:“法国荣光自民著,爱举义旗宏建树。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吁王虐政猛于虎,鸟合爪牙广招募。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囚奸蠢。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巳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这不仅是中国人第一次译出的《马赛曲》,也是中国人译出法文诗歌最早的一首。
王韬在《搜团老民自传》中对《普法战纪》的成书非常自负,认为在“虽仅载两国之事,而他国之合众缔交,情伪变幻,无不毕具”,山川地理,民俗风气,政治制度,亦无不备,“于是谈泰西掌故者,可以此为鉴”。该书最初是以“抄本流传,南北殆遍”,出版后士大夫更是争相传读,耳目为之一新。当时的洋务官僚、维新派人士都十分重视此书,曾国藩称王韬为“未易之才”.李鸿章认为他“识议宏远”,是一“佳士”。而丁日昌更是称赞王韬“具有史笔,能兼才、识、学三长”。陈桂士在《瞢法战纪》的序中指出“当今名公伟人皆誉之不容口。则是书之足传于后也”。缕謦仙史(即蔡尔康)在给王韬的另一本札记《瓮牖余谈》所作的序中称“《普法战纪》之作,其兵机之利钝、器械之优拙、疆域之险要,了然如指诸掌,谈西国形势者,无不奉为圭桌也”。二十年后.粱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列入此书。广为推荐,在《读西学书法》中把此书作为“皆足观”的纪事本朱体外国史,列为学习西学的必读书之一。
沈毓桂与培根的《新工具》
与王韬差不多同时在教会翻译出版机构中充当中文笔述者的沈毓桂也是值得一书的人物。
沈毓桂(1807一1907),江苏吴江人,字寿康,一生所用的笔名、外号多达几十个。少年家贫好读书,很早就成了地方上有名的人物,连“恃才傲物”的王韬也对他的才华表示折服。但他却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败北,于是只能长期在乡间设馆做垫师。1849年他由王韬引荐结识了麦都恩,并一度在墨海书馆当麦都思的汉文翻译的助手。一年后又回到家乡重抄塾师旧业。1859年他在沪与艾约瑟相识。因而再度来墨海书馆帮助传教士译书。林乐知在《褒扬耆儒奏折书后》曾这样叙述他的翻译贡献:“嗣偕墨海书馆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伟烈亚力诸君,编译诸书,如新旧约初刻本、英国志、释教正谬、天道实义、格致、化学、天文、算学、医理、性理等书约有三十余种。”除了墨海书馆译印的圣经、《大英国志》、《释教正谬》和《天道实义》外,还有哪些出自沈毓桂之手,尚待考证。但有一本与慕维廉合译的《格致新机》是可以确定的,即培根的《新工具》。
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严复是自觉地把培根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实早于严复20多年前,王韬的《瓮牖余谈》一书中就以长达800余字的篇幅介绍了培根的生平及其著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