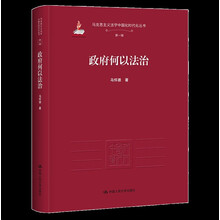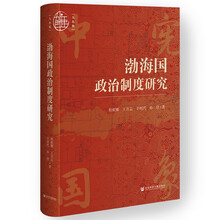阎红彦死后,被造反派称之为“云南的大党阀”、“阎老二”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首要目标。1月16日,造反派成立了“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17日晚,召开了十万人的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时隔五天,又召开了“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没有提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因这一“原则”分歧,昆明地区的造反派正式分裂了。由“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组成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后来人们称之为“炮派”;由“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等组成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后来人们称之为“八二三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示范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夺权的浪潮迅速推进到边陲省份云南。所谓“大联合夺权”,指的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所以,从一开始各派群众组织就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都自认为是“革命造反派”,理应夺权;都排斥对方,并欲摧垮之,以至演出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活剧。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两派大范围、大规模动用武力抢权,陷入了“内战”的境地。1月26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夺了省人委及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人马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同日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十万人“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两大派组织重复夺省委的权,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伴随着愈来愈浓的夜色,两派之间“谁是真革命派”的大辩论也愈辩愈烈。夺权!夺权!!夺权!!!在夺权声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瘫痪了,云南全省各级党政机构瘫痪了。各级“走资派”在夺权中被斗争,被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体罚。戴高帽游街还算得上是较文明的,更严厉的是披麻衣、戴白袖套、染黑脸,沿街示众。解放十八年之后的云南大地,“旧”的政权在不情愿中塌台了,而“新”的政权在纷争中难产。社会,处在动乱之中。然而,社会的管理不允许出现长时间的真空,现代社会尤其如此。2月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形势,研究对策。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别推选代表赴京。抵京后,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在接见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对干部要区别对待,搞“三结合”,要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做自我批评;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来帮助、推动实行大联合、“三结合”;革命造反派既要夺走资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你们要搞归口联合。赵健民等来到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面对着造反派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夺权导致社会动乱而忧心如焚的赵健民,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目的,在京期间主动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2月28日晚饭后,康生、关锋到了京西宾馆。赵健民因外出,未能见面。当赵健民回到京西宾馆得知后,立即给康生处去了电话。康生处的一位姓张的秘书将赵健民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南侧的西会议室。张秘书告诉赵健民,康生正在接见西安来京的造反派,请赵等候。赵健民一个人在会议室中静静地等候着。安静的环境使他得以集中精力思考着要汇报的问题。当汇报方案逐渐形成后,赵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点,1967年2月份即将成为历史。会议室内暖气有点过热,赵健民感到头有些发昏,不知不觉地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笔者不知道昏睡中的赵健民是否做过梦,是好梦还是噩梦。然而,这来临的3月的第一天,迎接他的将是厄运。3月1日午夜一时许,精神抖擞的康生来到了会议室。醒来的赵健民赶忙汇报问题。开始谈话的节奏较慢。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夜餐,康生边吃边听,赵健民也一块吃起夜餐,边吃边汇报。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端坐在旁边,认真地做记录。赵健民在扼要地介绍了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如阎红彦之死、两派对立夺权等之后,集中地谈了三点意见。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康生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赵健民话锋一转:“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赵健民停顿了片刻又慢慢地说:“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现在还在向造反派讲,可是没有人听。像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中的问题呀,还是理论不联系实际?”康生注意听着赵健民后面这句话。赵健民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想不通。”赵健民恳切地说:“对于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指不,中央现在应该三令五申。”在赵健民看来,他的这一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指示的,是正确的。几天之前,当他看到2月3日毛泽东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内容时,异常兴奋。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但赵健民没有仔细品味毛泽东同时讲的另一段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在柔和的灯光下,赵健民继续反映着第二点意见。“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七千人大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召开党代会有困难,如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据我个人了解,山东、云南两省党代会开得就很少。这样,领导干部很难得到党员、群众的监督,所以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多书记就下不了台。”“今后省、县和基层应多开党代会,使领导干部经常受到监督。平日多发扬小民主,就不会积那么多意见,这样大民主一来,领导干部就不会下不了台。”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