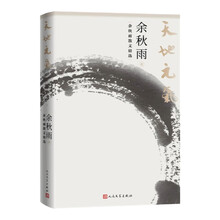我虽然不说《桥》与《英须有先生传》的文章技巧有多大的不自然处,但《枣》这一集中的文章似乎更自然一点。在《桥》与《莫须有先生传》中间,废名先生似乎倾注其全力在发挥他的文趣,希望过高,常常不免有太刻画的地方,或者是迂气,或者是钉恆气。在《枣》这一集中,幸而他还有一点写小说的欲望,在有意无意间来几句洒脱隽永的文章,遂有点睛之妙。但是在《枣》这一集中,也未尝没有使人憎厌的地方,其他的我可记不起了,现在只仿佛记得有篇题名为(四火>的,最后一段文章,是复述了一个民间的笑话,以鸡谐音为×(从尸从穴),在作者或许以为很有谐趣——或说幽默,但我们看了之后,总不免攒眉,以为恶札也。总之,大醇小疵,人人都有一些。
二 ○
一九三七年
一人一书(下)
三位女作家,论她们在文坛上声望的先后,该是冰心第一,凌叔华第二,丁玲第三。她们都写小说,也都以小说成名。可是对于冰心和丁玲两位,我却不想举出她们各人的一本小说来作为她的代表。冰心的小说不多,我不记得一共出版了几本。我自己只读过了《超人》和《往事》两本。我以为冰心毕竟是“五四”时代的作家,她的小说也只是开风气的作品。现在我们看《超人》一集中几篇作品,多少总觉得幼稚了。至于她以后的作品,题材总还是那么狭隘,感情总还是那么纤弱,若不是她那纯熟干净的笔致足以救济,或说遮掩了这种弊病,真是很危险的。冰心又以诗名家,可惜她的小诗又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品。《繁星》、《春水》以及后来的诗作都是一贯的绝句风的诗,仅有玲珑透剔的佳句,但不可能成为诗坛的奎宿。这种情形,我相信,或许正是女流作家的优点,但我既然不主张把男女作家的作品分两种标准来衡量,那么也只好委屈她们了。现在我宁愿推举《寄小读者》为冰心的代表作,这意思是表示我宁愿认她为一个散文家。因为一个好的散文家,可以奄有诗人和小说家的长技,虽然在(寄小读者》一书中有许多吟味中国旧诗的辞句,我还嫌她太迂气了一点。
从技巧上说起来,丁玲的小说无论如何总以<在黑暗中}为最好。《母亲》确是一部经过了长时期的考虑而写出来的文章,有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有所谓准确的意识,但是这些都依靠了一个真实的内容。她要写她自己的母亲的一生,这不是凭空虚构的作品。然而这并不是小说,这是一种新型式的传记。
现在我们要谈到凌叔华了。她是一个稀有的短篇小说家。我看过她三本书:《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
我以为凌叔华是一个懂得短篇小说作法的人。她的小说,给予人的第一个好感就是篇幅剪裁的适度。使读者,或是毋宁说使我,不感觉到她写沓太拖促了,或太急找了。在最恰当的时候展开故事。更在最恰当的时候安放了小说中的顶点。有几篇小说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结构(Plot),但也决不使人以为是一首散文诗,如冰心的《超人》中那篇《笑》和《最后的使者》一样。这种小说恐怕是间接地受了柴霍甫之影响,而直接地受了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及蕙儿荪(Romer Wilson)之影响的,我猜想。凌叔华的三本小说中,我投《花之寺》一票。
沙汀的小说,我只曾看过一本,他的处女作《法律外的航线》。最近出版的《土饼》,从前似乎曾经看见过编好的稿本,不知现在的是否仍是那一本的内容。为郑重计,我看就投了《法律外的航线》一票吧。
张天翼,不错,是一个讲究技巧,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确有特殊成就的作家。我们看张天翼的小说,总觉得流畅无阻,转折如意,故事的展开与进行,作者能够随意驾驭,一点不费力气,一点不着痕迹。而尤其在对话方面的成就,张天翼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个。有谁的小说中能有张天翼的那样不粘不滞的对话呢?我常常在怀疑着。不必在下笔时顾到小说的技巧,而自然显出了纯熟的技巧,这是宜僚弄丸的本领,读者万万不能以为他是随便写写的。但是张天翼也不是一个完善的作家,正因为他不必很艰苦地组织他的小说,他的写作态度有时遂不免于不庄。正如一个娴习的卖解女子,在半空中走绳索时,尚不免要卖弄风骚,向看客做一个俏眼儿,张天翼也常常喜欢在写作时弄一点不必要的文字上的游戏。例如把Chocolate译做“猪股癞糖”,把Turgeniev译做“吐膈孽夫”,把“恋爱了”说做“恋了爱”,把人名字取得很滑稽,把成句用在很不相干的地方,这种种故意逗读者发笑的小节目,似乎是张天翼自己最得意的玩意儿。而据我看来,却损失了他的作品的严肃性不少。这是一种写作上的最不好的倾向,不幸张天翼却洗刷不了这种弊习,每一篇里多少总有着一点。至于张天翼的作品,到现在已出版的恐怕不少了。若要我举一本代表作的话,我预备举他的《蜜蜂》。但这是得声明一句,我觉得张天翼的每一本小说,彼此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之所以举《蜜蜂》者,只是因为我对于这一集中的几个短篇,看得最熟,印象最深而已。
提到张天翼,我不由的要想起了听说如今流落在香港的穆时英先生来。这个人之显现于文坛,正如一颗彗星,而其衰落,却像梧桐之落叶,今日飘零一枝,明日飘零一叶,渐渐地至于柯残枝秃。我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有重发春荣的机会。现在且不必为他慨叹,我们应当谈谈他的作品。他和张天翼两人,可以说是同时起来的两个能表现新技巧的作家。张天翼善写士兵生活,穆时英善写都会生活。张天翼善写对话,穆时英善写都会中人的种种厌嫌的情绪。而两人的造句修辞都以轻灵流利见长,两人的小说都没有结构谨严曲折的故事。但在他们两人初起来时,读者都为他们的小说所风魔了。这就可证他们的小说在技巧及风格上的成功。
穆时英的为人和他的写文章的态度,可以说是很和谐的。他写小说,正如蚕吃着桑叶,东一叶、西一叶地吃进去,而吐出来的却不再是桑叶,而是纯丝了。穆时英不但曾袭用了日本某作家一段文章,在他的作品里实在还包含着别人的许多诗文。据我所知道的,他的小说中有许多句段差不多全是套用了戴望舒的诗句。我们若了解得他的小说的技巧和作风就是这种别人的好思想、好辞句的大融化,那么对于他的技巧和作风。也正不必怀疑了。
这一票,我有点投不定。反正都可以,现在就算投了一票《公墓》吧,但得声明这并不是表示《南北极》不如《公墓》的意思。
一九三七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