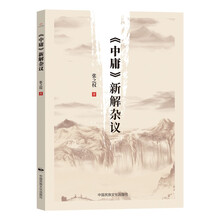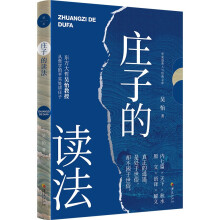捣毁旧制度老巢的历史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新一代制度文化变革者的肩上。这一代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历经磨难,前仆后继,终于推翻了大清王朝,成为名符其实的制度创新的一代。
依史家的定见,两代文化的分界线是在1894年。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康有为也说:“非经甲午之役,割台湾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康、梁两人不约而同地强调了1894年所具有的历史界碑意义。
1888年康有为赴京应试失手,乘便上书朝廷未果,郁郁南归,满腔的忿懑惟有诉诸诗文。他黜之于国而修身于乡,设坛讲学,以待报国良机。这是1894年以前的实情。不是康有为不努力,做事太离谱,而是火候未到,做事有点超前,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到了1895年,康有为于京都再度上书,一时间唱和者众多,据称具名者竟然高达1300余人(现存文献上的署名者只有603人)。秀才造反,里(朝廷)应外(社会)和,声势浩大,声震四海。这以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数番奏效,终于成就了摇撼中外、光耀史册的戊戌变法运动。时移世易,前后效应竟如此天差地别!梁启超、谭嗣同等康梁派的主将,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的首领,以及严复等启蒙主义者,也都是在1894年以后跃上并进而蜚声于政坛、思想界的。后来变更名称,如虎啸山林、风卷残云的兴中会也是在这一年成立的。谭嗣同顺应时势,从维新变法的反对者突变成为比康有为更为激进的康梁派的中坚、左翼,甲午前后判若两人,恰可视作文化代变的适例。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的“书”),洋洋18000余言,是早期跨代文化的重要标本。内中说:“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垂裳之势治天下。”“开创”而不“守成”,去除而不执持“华夏中心论”,在国际竞逐而不在自足封闭的环境中“治天下”,这确乎是康梁派、革命派与洋务派、此前的改良派分立门户的显著标记。
这一代破守成之势,光大前代于幽暗中闪现的思想火花,等视中西,谋本末俱变,创立创格的政治哲学体系,破坏和重建中国的制度文化。“批判的武器”不敷使用了便进行“武器的批判”,戊戌变法仆于前便有辛亥革命继其后,终于推翻了沿袭数千年的中国宗法君主专制政体,功在千秋。 然而,康梁派和革命派变政改制,取的是托古的手法,虽然也曾留意于开启民智,在一定程度上离了经叛了道,但是,他们托庇于古圣先贤,仍然企望承续老祖宗根本的道统成法,大都不敢大张旗鼓地非孔反儒,彻底地弃绝传统思想。他们不但无法与“五四”一代攀比,甚至还比不上同时代的严复、王国维和鲁迅等人。严复等人大力进行思想启蒙,“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其思想脉流直接“五四”思想革命的洪波巨澜。
第一节 颠倒道器和重释体用
要变政改制,开创新局,必须抓住前代文化变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理论上澄清“中体西用说”的是非,对前代文化变革实施批判,为变法扫清道路。前代文化变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理论上陷入混乱,在实践中守本固道。固道卫体,取用求器,避重就轻,动末不动本,这是前代“进亦忧退亦忧”的病根所在。为了解除这种病根,第二代文化变革者猛药施治,颠倒道器,重释体用,为变政改制启开了一条新的理论言路。
一、颠倒道器
康有为在攻击洋务派时问题是抓得很准的。他把此前的“变事”与现在的“变法”区别开来,主张“抓纲治国”,实施“本末并举”的一揽子“变法”政策。他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指出:“今天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损益四代,乃为变法。”他进而提议:由“皇上统筹全局,商定政体,自百司庶政,用人交外,并草具纲领条目,然后涣汗大号,乃与施行,本末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
梁启超对乃师的高论可谓心领神会,宣扬起来真是不遗余力。他说:“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皆畴昔人所谓改革者也。”梁所指斥的对象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和沈葆祯之流,认为他们“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于中国之弱亡之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梁在这里指出的所有弊端都是“变事”而非“变法”,他心中的“变法”是变本易俗,定出规模,统筹全局,谋本末俱变,这与乃师的意见可以说没有任何区别。
康梁派和严复对“中体西用说”的攻击的确击中了要害,是强劲有力的(严复的批判已具上文)。其中攻击欲最强烈、火力最猛烈者当为谭嗣同。谭必欲置“中体西用”论者于死地,不留一点儿回旋的余地。依从王夫之的“道不离器”说,他翻转体用、道器,将道置于器下,使器大道小,使器重道轻,使道依器而存,其真实的意图显然在于“用夷变夏”。你看:窃疑今人之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日:“无其器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
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是言也。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
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用行,器存则道不亡。
与陈独秀不谋而合,李大钊也把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与孔学视若冰炭,痛骂孔学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专制帝王之护符”,认定孔子之道与宪法风马牛不相及,“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吴虞也一样,他极力诋毁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宗法礼教,所依据的也是西方的民主原则。“五四”时期假西学非孔反儒的文章是相当多的,后来的学者论述“五四”非孔反儒的文章更是数不胜数,胜义纷呈,人们已很熟悉,笔者无甚新见,略示数例,不再繁述。
非孔反儒并非始自“五四”或“五四”前,而是古已有之,代不乏人。在以孝治理天下的魏晋,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隐居不仕,钟会请他出来做官,他不理不睬,一言不发,致使钟会悻悻而去;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却狂放不羁,故意醉酒两个月不醒,以避免篡得高位的司马懿向他提亲;颂扬“酒德”的刘伶,裸形屋中,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衣裤,竟问来访者何以入其裤中。明清两代的异端思想家李贽、黄宗羲、唐甄、戴震、龚自珍和俞理初等等,也都是惹人注目的非孔反儒的斗士。李贽以“童心说”抨击盛行于世的“官方”哲学——理学,即便对孔圣人也敢于口出不恭之辞。黄宗羲推原君民之关系,认为民为君本,意在从其义理根子上打破君重民轻、君权神授的天然神话。唐甄在《潜书·全学》中说:“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室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皆贼也。”大将、官吏和“众手”杀人,在他看来,均实为天子一人的“大手”杀人。戴震鞭笞宋儒,断定与道相通的理实存于人伦日用之中,拆穿了理学以理制情禁欲,实则是“以理杀人”的鬼把戏……
中国历代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想家非孔反儒,光耀天宇,辉映后世。“五四”前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他们那里吸收思想养料,表彰和张大他们非孔反儒的思想,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鲁迅一而再、再而三地称道魏晋文人纵酒扪虱、藐视礼法的“怪诞”言行,彰显“魏晋文章”“师心使气”的傲然风骨、慷慨愤懑的悲凉气度,是有来由的。周作人踏勘“五四”新文学的源头,找到了反抗压迫、高标个人性灵的明末小品。胡适以实用主义范围戴东原,说戴的哲学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是“中兴哲学的大事业”(《戴东原的哲学》)……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于晚清思想界的巨大影响:
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梁启超道的是实情,而且他之所道还远远不够,明清之际异端思想家非孔反儒的思想施惠于康梁派是多方面的,不过,由此而把它拔得过高也是说不通的,它对康梁派的影响毕竟只是精神刺激这一端而已。
“五四”一代甚至“五四”前一代与前此各代非孔反儒的最大区别,是其思想主张中含有现(近)代民主基质。嵇康辈的反礼教,诚如鲁迅所说,是迂夫子表面上的反礼教,是爱极生恨的迫不得已,是佯装的,他们在骨子里还是把礼教当宝贝看的。李、黄、戴破口大骂宋明大儒和君主,似乎无所顾忌,无遮无拦,甚者直将矛头刺向了孔圣人,但说句实话,他们走得并不太远,他们的思想还仅仅停留在民水君舟,载舟覆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水平上,与“五四”前一代基于个体自由的民主思想不是一码事,还不能相提并论。候外庐拿西方的启蒙主义与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想相类比,称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想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恐怕不一定很恰当。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分属两大不同的文化系统,各有各的生存土壤,各有各的特色,是不好拿来进行简单类比的。前者是在肯定君主专制的前提下非孔反儒,是“大骂大帮忙”,期盼的是回复三代和明主再世;后者则是在肯定个体自由的前提下主张否定封建制而建构民主制。黄宗羲、唐甄以及顾炎武都反了“水”,于晚年重返圣道,“慎独”的慎独,养性的养性,续宋学主脉的立朱子神祠,都寻得了他们必然的归宿。他们理论的叛逆性没有能够越出民本思想的限域,超前性也没有达至康梁时代。至于龚自珍和俞理初,他们尚未闻到鸦片战争的硝烟便长辞人世,其非孔反儒的思想虽未与身俱亡,却也很难说有着现代民主的基质。
真正开始把现代民主思想作为孔儒学说的敌对面并用它来非孔反儒的,是变政改制一代,自那以后才蔚成风气。就规模大小和自觉程度而言,“五四”前一代非孔反儒自然无法与“五四”一代相比,但是,就深度和激烈程度而言,却未见得逊色多少。他们非难孔子,采用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只是像“五四”一代那样直斥孔子者尚不多见。这当然情有可原。国粹派领袖章太炎就是尚不多见者之一。他的《论诸子学》从道德角度非孔反儒:
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
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鲁国巧伪人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则儒家之真可见矣。
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
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无实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