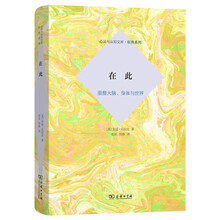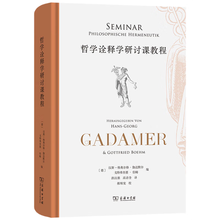这种非知识的地带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第四种历史时刻,虽然它在另一个不同意义层面作为当今历史主义和人文科学的照相底片与它们同时存在。因此,我们就有了第三种“过渡”,假如可以的话,我们依然可以将它称作展现的(或者甚至是辩证法的)第三类问题。虽然这第四种时刻偶尔也可以在预言模式中产生共鸣——著名的说法“人类从沙滩上消失”,某些新的、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和生活发生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昙花一现,后来人们在列维一斯特劳斯以及德里达思想中找到一些影子——更常见的是,人们从我们自己的体系的角落里探寻(并找到)了它:例如,对那些杰出的疯子进行重新发现,像赫尔德林和阿陶德;强调语言的审美成分,使之超越资产阶级意识,使它充满存在事物,不仅仅能够用于指涉意义,而且能够强调意义的限定性,或者超越意义。这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做法与莫里斯.布朗绍(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提到)的审美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看到了它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差异(虽然两者都具有严肃意味)——因为,那片得益于海德格尔本体论和诗学光辉而显得透亮的空地在这里变得像黑洞一样黑暗而不详。当然,如同在海德格尔那里的情况一样,这里以预言方式提出的要求——既像迫切的请求又像乌托邦视角——就是要战胜人文主义。然而,我们依然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顶峰时,日本人曾不无灾难意味地宣称“战胜了现代性”,上述一切是否就是同一回事?
这个问题将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两个断裂,回到福柯和海德格尔,也回到了两种现代性的神秘性。海德格尔一直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发展至今的整个过程早已隐含在笛卡尔的思想中,这种观点实际上掩盖了某些东西,而福柯则使那些被掩盖的部分变得昭然若揭。在福柯的阐述中,海德格尔的叙事仿佛被分成了两个断裂的时刻:第一个提供了简单展现的现代性,即把世界首次或者“科学地”翻译成数学图表和图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