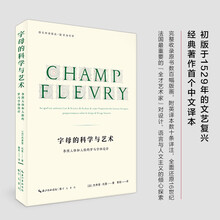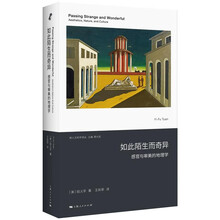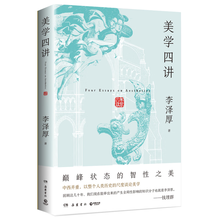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美学(上)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虽然就社会来说,它是一个极其动荡的年代、黑暗的年代;但是就审美与艺术来说,它却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年代。相对于此前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发展的突破期,这个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觉醒上:一是美的觉醒;二是艺术的觉醒;三是自然的审美价值的觉醒。而这三者又都立足于人的觉醒上。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玄学的产生有很大关系。
第一节 玄学美学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中。《老子》第一章论道,说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年间,由于社会黑暗、动乱,不少知识分子出于避祸,遁入老庄,他们以讨论《老子》、《庄子》、《周易》三部著作自娱,这三部著作当时号称“三玄”。于是,研究讨论这三部著作的学术也就称为“玄学”。玄学明显地是对汉代经学的反叛,给学术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但是玄学并不抛弃儒学。事实上,参与玄学论辩的玄学家们的基本立场是整合道家与儒家。“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是玄学的基本矛盾。只是这种整合,有的以自然整合名教,而有的以名教整合自然。玄学并没有直接讨论美学的问题,但玄学中的论辩却与美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有无之争
有无是玄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两个不同的学派:一派为“贵无”派,代表人物为王弼(226—249);一派为“崇有”派,代表人物为郭象(252—312)。
问题的由来是对《老子》第一章中关于“道”的基本性质“无”与“有”的理解。《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里有个问题,道,归根结底是“无”还是“有”?老子在这个问题上谈得不是很清楚。正因为此,就出现了王弼的“以无为本”和郭象的“有物自造”两种相对的观点。
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日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王弼《论语释疑》)《老子》虽然说“无,名天地之始”,但并没有说道就是无。王弼将老子的理论向前推了一步,将“无’’视为“有”之本。具体来说,“无”与“有”之间具有这样三种关系:第一,宗主与统属的关系。王弼认为“无”是宗主,万物即“有”为“无”统属。他说:“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王弼《老子指略》)第二,“一”与“多”的关系。“无”是“一”,万物为“多”。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老子道德经注.四十二章》)第三,“兼”与“分”的关系。“无”是兼,所以“不温不凉,不宫不商”;“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老子指略》)无所具有的兼的性质,使得无可以“包通天地,靡使不经”(王弼《老子指略》)。王弼总的观点是:“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王弼《老子指略》)
明确地将“无”作为宇宙之本对中国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打破了主客两分的模式,强调物我不分,我即物,物即我。这种物我合一正是审美的巅峰体验。二是将空灵、虚、无限作为艺术意象的最高追求,这就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境界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崇有派认为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崇有派的代表人物郭象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郭象《庄子注》)按他的看法,就是“物各自生”。这种“物各自生”,郭象称之为“独化”。“独化”论发展庄子的物各有其性的思想,强调“物皆自然”。应该说,这种理论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将“物皆自然”绝对化又有些不妥。毕竟物与物之问还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物的变化既是自性使然,又是他物作用或转化的结果。
郭象的崇有派与王弼贵无派之不同,主要在于王弼将宇宙本体定性为无可把握的“无限”,而郭象则将宇宙本体归之于事物的本性。这两种观点都可从老子、庄子那里找到源头,只是老庄认为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郭象的“玄冥”说与王弼的“以无为本”说有相通之处。所谓“玄冥”来自《庄子·大宗师》:“于(wu)讴(ou)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郭象解释说:“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郭象《庄子注》)意思是说,“玄冥”是一种似无又非无的混沌状态,可以将它看作万物“独化”的境界。“玄冥”这种境界与王弼说的“无”相似。
崇有派在美学上的影响主要在强调事物的本色为美、本性为美。郭象说:“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庄子注》)如果说,贵无派的“以无为本”说是中国境界说的理论基础之一,崇有派的“独化”论,则是宋代黄体复“逸格”说的理论基础之一。“逸”作为艺术品评标准中的最高标准,其根本点在于“得之自然,莫可楷模”,而这正是郭象所强调的“各称其事”、“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
二、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热衷讨论的又一个问题。言意之辨出自《易传》,《易传》讲八卦的由来,说是圣人认为“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就此命题展开了讨论,基本上是“言尽意”、“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三派。据欧阳建《言尽意论》介始,魏时人伦鉴识就引用“言不尽意”论。说是“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欧阳建认为意是可以尽意的。他说:“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尽意论》)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不是讨论语言的功能问题,与语义学关系不是太大,它主要是讨论宇宙本体的问题。根据《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观点,王弼等一批玄学家认为作为宇宙之本——“道”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在这个基本立场上,他们的具体看法有别。曹魏时名士荀粲认为,不仅言不能尽意,象也不能尽意。他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能举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