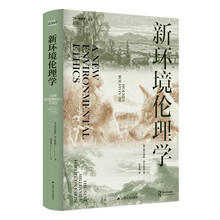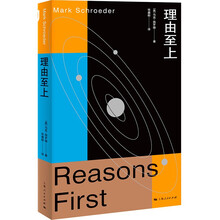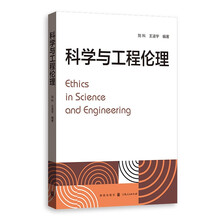正因为如此,人能够坚守善性,力行善举,也与他能够分辨出恶之为何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道德的行为抉择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存善祛恶的道德辨析问题。宋明理学家特别强调的道德问题,“存天理,灭人欲”,就鲜明地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善性善行呵护问题的极度重视。
第二,在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上,儒家伦理对组织的伦理原则和组织的理想范式进行了殚精竭虑的思索。
儒家伦理对社会组织的关注,较为忽略它的利益基础,却非常重视它的伦理原则,尤其强调以人的善良品德与善良行为的培养,去营造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以求为社会的道德化提供一个良性氛围,促成每个人德性的完善。这一观念的展开历程是这样的:首先认定人的行为是受德性驱动,而不是受利益支配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是也;其次确认社会组织只需依靠道德法则即足以保证其顺利运转,所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再次肯定社会组织的最高道德原则就是培养道德完善的个体,而这类人物是不为物质所动地践行伦理规范的,所谓“孔颜乐处”,“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③是也。三个层面次第推进,逐步提升,终于将社会组织的原则净化为纯粹的伦理规则。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儒家构想出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一个十足的伦理王国。伦理王国的最理想状态便是人皆具为公之心并选择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同”。
第三,从对事物与经验的内在价值的可期望性来看,儒家伦理非常注意五条件善性的至上价值。一方面,养成“浩然之气”,达到“至大至刚”,臻于完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在道德践履的活动中,对那“一念不善”,须“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①,由此才能“做个人”。倘若不将五条件的善的知识与行善的能力呵护住,那么,恶的肆虐就难以避免,“心中贼”、“山中贼”势必横行。
很显然,儒家伦理的讨论主题完全属于规范伦理学范围。相反,对管理伦理学的主题则没有涉及。管理伦理学主要围绕的中心议题是,企业管理中道德因素是如何转变为劳动生产率的,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重要主题,诸如:人际关系与劳动生产率的微妙关系,管理者与企业、社区、用人道德与权力的关系,管理过程中的原则、规范和范畴的体系,以及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评估方式。①管理伦理学的研究主题,指向的目的明显的是:合理地组织劳动,以理性地利用道德动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从上述分析可见,儒家伦理论述的道德规范,表现出强烈的应当性(ought to be)、绝对性(absolute)和命令性(obligation)。在儒家伦理的视界中,道德的善是不容商议和思量的最高最后规范。而积德行善也不能假借任何外在功利(尤其是物化性质)的支持,去做善事,践履善的规范,纯然是道德命令而绝对不是道德劝谕。因此,道德价值也就成为至上的、中心的价值观念,并且超逾现实事实世界,一切偏离道德轴心的思虑与行为都是恶的。相反,管理伦理学处理道德问题时,则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material gain)、相对性(relativity)和商谈性(discourse)。管理伦理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的,因而分析道德问题不只是为了道德的理由,更主要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因此,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势必极度重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互动关系,而不能单纯地以己度人,对话、协商、沟通等商谈的伦理行为规则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五条件性和有条件性,划分出了儒家伦理和管理伦理学的界限。并且,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导致社会要素的伦理化,使伦理成为固化现世社会的封闭架构(closedstructure),而管理伦理学促进伦理要素与社会各要素的健康互动,营造成一个改进现存社会物化状态和精神构成的开放系统(open system)。可见,作为古典规范伦理学的儒家伦理,是内在地不具备管理伦理功能的。
当然,从一般伦理学理论的逻辑关系上来讲,管理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是规范伦理学应用于实际的道德问题的理论成果。①因此可以说,儒家伦理理论尽管在类型学上归属规范伦理学,但它并不先天地缺乏应用于合理地组织劳动的管理伦理的处理能力,只要外部条件具备,儒家伦理是可以搭起规范伦理与管理伦理间的桥梁的。但是,理论假设依靠经验事实的支持。儒家伦理生成的原有社会文化基础,并不具备发挥管理伦理功能的外部条件。
儒家伦理文化的社会学分析告诉我们,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只能供给儒家思想家们建构规范伦理学体系的各种条件。
作为一个等级社会,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血缘关系的亲疏凝结而成的,尊卑贵贱,由老少、长幼、远近、亲疏所注定,不容许个人选择的自由,而“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乃至业缘——引者加)不过是血缘的投影”①。正是因为如此,儒家伦理尽管在一般伦理规范的申述中强调“泛爱众而亲仁”②,但是,从“事父以孝,故忠可移于君”的社会伦理规范上看出,也能够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③的主张中觉察。作为一个乡土社会,古代中国人全靠农业谋生,“黏着在土地之上”,从而造成了人和空间关系上的不流动,人和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由此,为增加效率的合作消逝了,人们之间的协作只不过是基于血族情感的助人为乐罢了。作为思维方式上的笼统特性,分析问题时的定性方法,以及从原则到问题的演绎逻辑,则阻塞了伦理思路通向分析化、精确化、定量化、归纳统计化。因为,在一个以应当、好坏(是非、善恶)等抽象的普遍原则为时尚的社会里,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当然会相对忽视各种问题的具体条件性,无视各类问题的精确测定与数量关系,更不用说概率统计了。这恰恰使合理的劳动组织最需要的资源处于匮乏状态,既抽掉了伦理思维趋近健全的动力,也丧失了现实社会合理组织的伦理动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线索所结成的网络,自食其力成为每个人生存的基本状态,很少感到需要伙伴,与别人发生关系总是后起的和次要的,并不需要经常的和广泛的团体。这种社会能够获得广泛认同,因而具有极强伦理感染力与影响力的规范也就是私德规范。如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或“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而管理伦理学的生成土壤则不同。职业社会、工业机制、分析思维、定量核算、归纳方法、公共道德等“现代”西方社会要素为管理伦理学的发生及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职业社会是超血缘的。在职业社会中,人们的劳动仅有分工的不同,而无贵贱的差异,固有的血缘世袭传统不对现存工作起保障作用。而职业的分化日益复杂细微,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合作向紧密的方向发展,使人与人之间往来更具繁复性,单纯依赖人际情感已不足维持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因此,人们需要以契约的方式清楚地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货币为媒介的精密计算成为合理化行为的标志之一。这就势必要求伦理学为每个人的公乎发展提供论证,要求管理者为每个被管理者提供合乎道德的发展机会。工业机制,则将生产按需要区分为细微而具体的生产流程,这种机制,自然地要求伦理学注重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管理者的道德状况、管理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管理者本人与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工业化成为管理伦理学发生与发挥作用的最强、最直接的动力。同时,随工业发展而备增的物质财富和新鲜世象,随科学分门别类对自然现象的人微研究,随统计手段的日益精确和完善,分析思维取代了综合(笼统)思维,粗略统计被定量核算所代替,演绎方法日渐走向归纳方法,这既为伦理学走向精确的分析伦理学提供了动力,更为伦理学进人工业企业管理的领域开辟了新境地,当然也就为整体管理活动的优化提供了伦理动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式的工业(职业)社会,其基层结构是一种团体格局。在这种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立在个人——团体的关系上。团体格局以笼罩万有的神为赏罚的裁判者、公正的维持者、全能的保护者。管理者作为神圣规则的代理人,也只能依循公正原则行事才能保有代理人资格。这样,权利观念产生了,权利有力地限制权力。为防止权力滥用,宪法诞生了。国家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公民以尽公德为国尽忠。于是,公共道德成为主流德行规范。这无疑推动了思虑公众人物的管理者的道德规范的管理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以及发挥强大作用。
综上观之,儒家伦理的生长均不具备这些“现代”条件,因而,它打不通规范伦理学走向管理伦理学的渠道。
(四)作为可能的普世伦理的中庸
中庸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既成史上的失落,是否意味着这种德性观也应当放人思想的历史博物馆,仅仅具有思想或知识的考古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诸如孔子、子思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对中西文化发展发生了深入而持久影响的大哲所具有的智慧的信赖。这种影响,表面上已经体现为他们的思想在社会历史的不同侧面产生的效用。深一层讲,则体现为随着人类处境的变化,这些思想所表现出的适应时代需求的活性特征。另一方面,当我们追问为什么在中西文化的“轴心时代”,大哲们“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中庸的德性观时,我们会进一步思考,难道这仅仅是一个思想史的巧合吗?抑或是由于他们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中道对人类社会健全运作、逼近理想之境的不可或缺性?我们倾向于后者。因为,随着人类社会当代处境的日益明朗化,中庸观作用的外部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于近古与现代。可以说,外部条件的变化正引起德性观念的重构。而普世伦理的提出,正刺激着人们以最可能成为普世伦理的传统资源的中庸德性观,来重新定位中庸的德性价值。
有利于中庸德性观从古典观念转变为现代规范的外部条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确认。其一,当代人类社会为一多元社会、全球化社会。多元社会意味着承载不同价值,有着不同传统的民族、国家可以和谐相处。全球化社会意味着和谐相处的社会——政治——文化有必要谋求一个与此相适应的规范体系。这一当代状况,是历经近代充分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之后,才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讲,多元只是一种共处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共谋发展的格局。但是,多元观念的互动,为健全可行的普适规范的诞生,提供了必须条件。如何在多元间推衍或发展出多元共适的普适规范体系,就需要以中道为原则,平心衡量。这对走出反中道的某一文化中心论,达成真正具有人类性的普适规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此,中道不单纯具有德性意义,也具有一般方法的价值。可以说,多元社会格局直接推动了中庸价值的复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