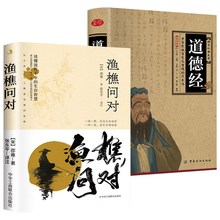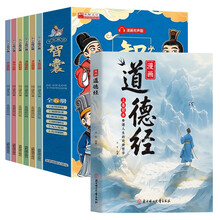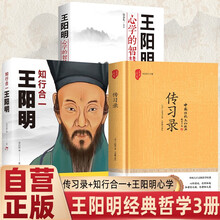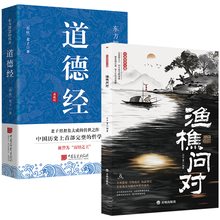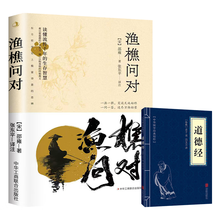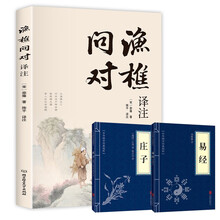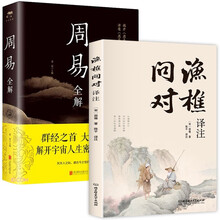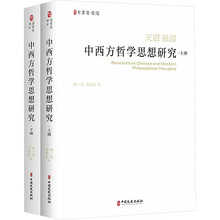显而为易见,玄学虽是特定时代的哲学现象,但是,在中国哲学史的长河中,它并非孤立的现象。换言之,中国哲学史的长河中,波浪虽有大小之分,但它们是互相紧密关联、缺一不可的。玄学可谓长河中的一个大波浪。基于这一设定,有从“清议”、“清谈”、人物评价与“玄谈”的关系出发,把刘邵的《人物志》作为魏晋玄学先驱的研究。但是,这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绝不是全部。
作为一种哲学现象的玄学,在形式上,主要是依据《老子》、《庄子》、《周易》的一些思考方法来展示自己的想法;在内容上,则以老庄释易,或以儒明道;在本质上,可谓儒道融合的产物。当然,这仅指思想的特征,而不在于强调儒道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一事实本身。实际上,玄学是许多流派思想整合的结果,关于这一点,笔者想通过体味王弼以下的论述来进行分析:
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物失所载,未足守也。然致同途异,至合趣乖,而学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观其齐同,则谓之法;睹其定真,则谓之名;察其纯爱,则谓之儒;鉴其俭啬,则谓之墨;见其不系,则谓之杂。随其所鉴而正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故使有纷纭愦错之论,殊趣辨析之争,盖由斯矣。(《老子指略》)
在王弼看来,法家“刑以检物”、名家“名以定物”、儒家“誉以进物”、墨家“矫以立物”、杂家“杂以行物”的行为,必然导致“巧伪必生”、“理恕必失”、“争尚必起”、“乖违必作”、“秽乱必兴”的结果,其原因是它们都“用其子而弃其母”。对此,只有道家的“因而不为,损而不施”,才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不难推论,王弼自身推重儒道融合的思想特征本身,也是在批判吸收众多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绝不限于儒道本身极小的范围,而有着深广的思想渊源。
在理论的层面上,其次,想探讨人性(性和情)、“义”与“利”、“公”与“私”、“富贵”与“贫贱”、“死”与“生”等范畴问题。当人对天人关系或万物的相互关系的思考达到较深的地步时,自身就自然成为思考的对象。事实上,天人关系中的重视人、以万物自身作为一切存在之本的观点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具体地说,例如,人为“天”所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其本性或本质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在价值判断上,本性是善还是恶等,从对外在物的认识转向对自身内在方面的认识,这是人认识的深化。从与天人关系里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源问题的紧密关系来看,首先,论述人性。此外,人为了维持生命,对物质性的东西以及利益的追求是不可或缺的,这些行为并非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切人的行为。当然,由于人们实际上是共存的,所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产生。因此,与利益的追求相伴随而产生的还有利益追求本身是否恰当的问题,贯穿这问题的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再者,人由共同体那里获取属于自身的利益而被赋予相应的对他人的义务,因此,紧接着分析“义”与“利”的问题。主体行为以集体、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目标,还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成功、利益,而无视集体和他人的利益,抑或以天下所有人的需要的满足为最高价值,或以个人乃至家族欲望的满足为最高价值,无视他人和共同利益,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物等等,这是反映个人和他人、集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公”与“私”的问题,在此将进行探讨。在生活实践中,行为主体应对利益和履行的义务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对个体来说,从共同体那里获得的利益和地位也不一样。基于此,形成了现实生活中的“贫”与“富”、“贵”与“贱”的实际差异,那么,“贫”与“富”、“贵”与“贱”具有什么样的实际关联呢?接着将以此为问题。对人来说,既有“生”也有“死”;“生”是开始,“死”是终结,生死是始终。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并非无限制。所以,人对自身的生死持有特别的兴趣,例如,“生”是什么?“死”是什么?人面对生死时应采取什么对策?人依据什么来使“生”有意义,“死”有价值呢?能实现生命的不朽吗?这些是人生最高的问题,所以,在范畴的最后进行讨论。
在实践的层面上,则究明道德教化、道德修养、理想人格等问题。社会共同体是个体人的集合体,离开人的存在,这共同体就不复存在。共同体本身为了成为良性的共同体,各个个体的共同协力是不可缺少的,为了实现这协力,其共同体的价值观的养成就成为必须。另外,在现实生活中,要完全杜绝恶是不可能的,正因为风俗有趋坏的危险性,就有醇化风俗的必要。道德教化可谓养成价值观和醇化风俗的最佳选择。为了切实有效地施行它,就不得不考虑教化是否可能、以什么样的人为对象来施行教化、依据什么原则来实行教化、为了获取理想的效果,润滑教化的方法是什么等等的问题。在此,首先分析道德教化对治世和人性良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对象、原则,以及为了激活自身功能的活性化等实践问题。
对个体来说,后天的道德养成是不可或缺的,这在上面已经论述。但当我们考虑具体的实践时,在接受外在道德教化的同时,施行自我道德修养显得十分重要。《礼记·大学》载有“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重视修身可谓人的共通点。不言而喻,道德教化的目的是通过向人解释当为的行为,来启发个体的自觉,养成良好的德性。这一目的的实现,除跟道
德教化本身的科学合规律性有关系外,就将系于个体能否自觉履行从道德教化处获得的道德情报。但是,对个体来说,从道德教化处获得的道德情报,在终极的意义上,不过是他律的东西,如不能变他律为自律,道德教化就难能实现预期的效果。接受道德教化而施行道德修养,是把他律的道德原则涵养成个体内在的道德性的重要手段。换言之,在道德教化和个体的道德性
之间,存有道德修养,修养是由教化成就道德性的桥梁。而且,在动态的层面上,在具体道德实践的行程中,个体在接受道德教化的同时,施行自我修养,既可以配合道德教化,乃至巩固道德教化的成果,又可提高个体道德养成过程的润滑度。总之,从道德教化的相关性着眼,在此分析修养的原则、方法等问题。
在现实生活里,个体的精神面貌或人格形态是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这虽有人性的因素,但主要是后天道德养成成果的自然反映或自然凝聚,换言之,在道德的层面上,这实际上也就是现实人格的问题。另一方面,有效地把握道德教化和个体自我修养,提高道德实践的功效,给个体提示一定的理想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基于此,探索理想人格是必要的。换言之,理想人格既是来自教化和修养效果的具象,又是理想的道德境界,所以,最后论述至人、圣人、大人、君子等具体人格。
综上所说,刘邵以仁、义、礼、智、信为人性之常,显示着性善论的特点,从他关于人性总体的构造来看,“中和之质”是其性情论的哲学基础,“爱敬之诚”则为其心理机制。本性之常既离不开“中和之质”的决定,也不能没有“爱敬之诚”的支撑,两者的共作互动才是其价值实现的关键。从两者的内在关系来看,“中和之质”离开“爱敬之诚”的附丽和支撑,就无法对来自性情“处上”的危险性进行合理调节而实现五常本性的价值;另一方面,“爱敬之诚”如脱离“中和之质”的根基,也难以开出人性的绚丽花朵。
概言之,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上,阮籍强调“保身修性”,其目标设计是“长生”,具体的修养方法则是“逍遥”和“齐万物”。这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人人格境界的精神窗口,但毕竟有逃避现实、抹杀万物之间客观存有的差异的嫌疑,因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缺乏积极的意义。所以,在社会的层面上,这种逃避现实型的思想正好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另一方面,审视当时积极性的行为方式本身危及生命这一事实,逃避现实无疑是当时社会保身的最有效的手段。诚然,阮籍思想酶理论和现实的价值判断,存在着二律背反,这也是不能无视的。
以上对“真”、“性”、“命”、“礼”、公私等道德概念分别进行了分析,显然,它们并非孤立的概念。在郭象道德概念的系统中,“真”是基本的概念,对“真”来说,在个人方面有“性”和“命”等概念,在社会方面有“礼”和公私,“真”的精神贯穿于其他一切概念
之中,其他概念不过是“真”的本质的具体展开。在个人方面,本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无法改变的自然性,它要受本分的制约,本分是生来就有的,本性必须在本分的轨道上运作,守分是全性和实现个体价值的条件。本性具有“感物而动”的特性并持有仁义的素质,这赋予“习以成性”以必要性以及“成性”在本分范围内的可能性。无疑,这具有消极被动性。另一方面,“各令自得”又给人们展示了赋予个体以积极主动性的图画。这也体现了激发客体践行自得的责任性。从“物离性以从其上而性命丧”来看,本性是生命的本质和源泉,生命则是本性的具体展开。要言之,本性是内容,生命是形式,守分则是统一两者的桥梁。关于命运的“命”,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接受它的安排,这是来自外在的对于人的先天的限制。
总之,本性中的本分和命运的“命”都是先天赋予人的规定,两者的相异处在于本分制约着本性,命运的“命”则超越性分直接制约个体。换言之,个体的本性受着本分的限制,个体自身则受着命运的制约。也就是说,本性必须在本分的范围内运作,个体则必须在命运的领域里努力。本性决定于本分,个体左右于命运。
日本汉学家中岛隆藏认为,郭象的自得有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是用自己的自得去成就他人的自得,低层次是借助于他人的自得才能实现自己的自得。郭象在两种自得中强调的大概是
后者,这也成为东晋思想界流行的倾向。从中岛引用的资料来看,高层次的自得即“体神居灵而穷理极妙者”(《逍遥游注》,页30),也即圣人的自得。低层次的自得是个体“各得其实”(同上,页26)的自得。这不得不说给郭象的自得研究注进了一股新风。可以说,这是分析基于不同个体的自得而得出的结论。笔者在此分析的是同一主体在不同场合的自得具象,即内在性的自得(足于所受)和外在性的自得(安其所司),贯彻自得行为始终的是自然无为的精髓。
郭象认为“生以养存”,强调道德修养,多少给他性分自足的围墙开了一个供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窗口。修养也就是养生,包括养身和养心两个方面。对个体来说,身不属于自己所能有,它是自成的。人虽无法改变生死的事实,但可通过养生来丰富人生,完全实现生命的价值,即“尽年”。而养心的关键是不用心。养生的具体操作方法是“任朴而直前”、“静于性而止”、“坐忘任独”、“守其自得”,贯穿于这四者的一条红线是自然无为。这四者自然构成实践的操作链,自得是其主导链,由它连接其他链,其他链则为分子链。换言之,自得的精神贯穿于三条分子链中,分子链是主导链的具体体现。但是,自得的良性运作和价值的完美实现离不开其他链的共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