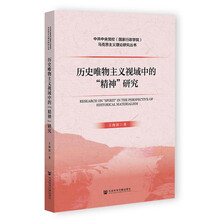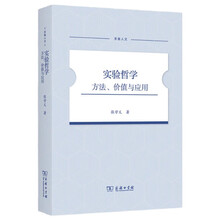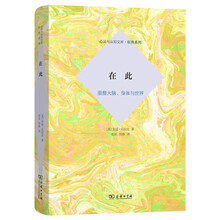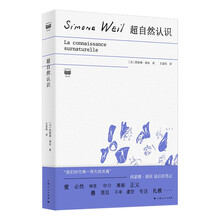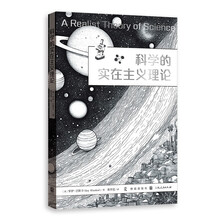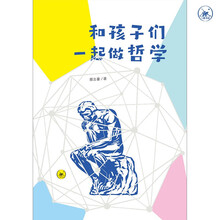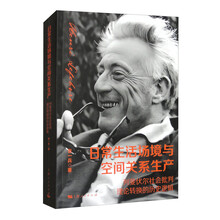不过,布吕歇尔的这一“站”并没能让阿伦特“站”回来。阿伦特通过各种复数行动实现自我凸显,迫使人们,尤其是海德格尔,接受她的思想与判断的特性。②在阿伦特的眼中,对独特性的要求构成了人类生命的极点(她将这种要求追溯到自己常常致以热烈敬意的邓斯·司各脱③),但她从不以此为妇女的特性请愿。
对政治学的激情、对出现的兴趣,构成了阿伦特出生以后人格之中阳光的一面;结识布吕歇尔后,她的这一面得到了充分发展。一边是在历史上迷失了方向的孤独哲人(海德格尔),另一边是在政治学中迷失了方向,却凸显出“叛逆生命的真实性”的狂热小丑(布吕歇尔),汉娜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在两者之间挑选一个,或者简单地将他们混为一谈。对于她的这些身体伴侣、精神伴侣而言,至少从他们为她而在的角度讲,她也同样是创造者。作为政治学“教授”,海因里希从深奥的哲学中,从妻子生命的精确性之中学到了很多:他们的通信证实了两人的对话已经悄然丰富起来。相反,海德格尔阅读阿伦特的作品后所表现出的淡漠——甚至缄默——说明他这个“职业思想家”并没有从他年轻的学生那里受益。不过,从他们已出版的通信来看,两人在晚年曾有过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交流。战后,托特瑙堡的智者是否利用了他在效力于纳粹主义之前的情人的社会地位呢?阿伦特是不是想通过接近海德格尔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扎根于基本传统,在传统思想中留下印记而后再摆脱束缚呢?归根结底,就像在希腊的辩论会场上,或者在一个观众既做评委,又即兴参与戏剧演出、进行再创造的舞台上一样,汉娜·阿伦特建立了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新颖思想:既涉足行动,又维护退缩行为。
许多与她同时代的人都证实了她身上的女性魅力——在纽约的沙龙里有一些人思索着这个魏玛共和国的怪女子①;也有像汉斯-约纳斯(HansJonas)那样的,对这位女性朋友颇为欣赏,因为在成为“本世纪最有思想的女性之一”的同时,阿伦特仍能“享受男人只为女人保留的关注”。她既非“思想家”(这是一个以偏盖全的定义),也非“人”(这个字看不出性别),而是“女人”,约纳斯强调说。②然而,只有受到强烈刺激时,阿伦特才肯为女性的状况冒险抗争:她是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比女权主义者更有女性特质呢?其实,她并不认为支持女性“事业”是正确的。③如果有人告诉她,哲学家这一行主要是男人干的,她仅仅会说,“有那么一天,很可能会出现一位女哲学家”,并且不忘表明,那个人不会是她,因为哲学家群体并不接纳她,她本人也只把自己定位在“政治理论”方面,有时甚至是一名“政治记者”!“发号施令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正因如此,她才应当尽量避免陷入这种局面,尽管她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女性特质。……对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产生任何作用”,④对那些坚持要求她对女性解放斗争作出表态的人,她如此作答。
不过,她既不会发号施令,也不会俯首听命。事实上,某些人用以形容“女性”的雌伏,在接受耶路撒冷审判的艾希曼(AdohEichmann)身上,表现为思想缺失,或称“平庸的恶”。阿伦特从这个纳粹分子身上揭露的,是否正是这种言听计从的“伪女性特征”呢?她发现,艾希曼并非愚蠢透顶,而是平庸可笑,缺乏思想。其本人并未下达那些卑劣的命令,而是满足于屈服和传达。艾希曼是不是一种“非人”、一种“伪女人”、一个小丑呢?“我看了警察长达3600页的审讯资料,看得非常仔细,我竟不记得自己笑过多少次,哈哈大笑!……我临死前恐怕还要再笑上3分钟。”①
可是,如果既非发号施令,又非俯首听命,既非施展影响,又非服从屈就,那么究竟应如何定义女人呢?“对于我来说,最基本的是理解——我必须理解。我的写作也属于这种理解,它本身也是理解过程的一部分……当别人也能理解时,我所获得的满足感不亚于重返故园。”②这种“理解者”的谦逊态度揭示出丰富的隐含意义。理解者等待,接受,欢迎:虚怀敞开,她任人停靠,她接近,她是相随相伴的,她拥有泰然的“自由放任”的基质(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泰然任之”),并且这种基质自由繁殖。不过,理解者也会索取:她选择、夺取、糅合、改变因素,将它们据为已有,并进行改造。理解者与他人共存,同时拥有自己的选择。她创造新义,但从中又可窥见被转变后的他人的见解。而这个从思想到行动的建构一解构过程,则由我们来辨别。
我们能否举出一部作品?当然可以。根据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习惯,阿伦特毋庸置疑地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政治作品?哲学作品?女性作品?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予回答)的作者。其中可以看到她犀利、简洁、紧凑、旁征博引却又语焉不详的文风;她的重复与混杂激怒了各方面的专家;但正是由于阿伦特的风格植根于她的个人经验和时代生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