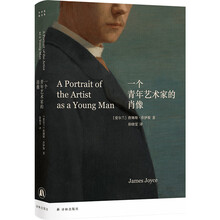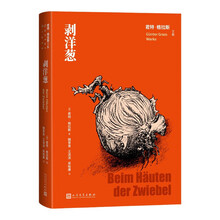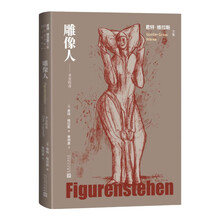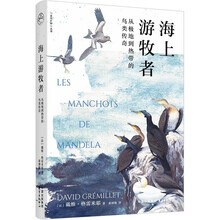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那儿去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见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久。
“你干吗站着?”他过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诗你读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只能说挺傻的。”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十七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我怎么不能读你的诗?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的诗作?有几首诗我甚至很喜欢。我很想听听行家们的评论。所以我抄下了你的诗,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你抄了哪些诗?”
“所有的诗,”父亲回答,“我不仅仅尊重我理解的东西。我让人判断的不是我的鉴赏力,而是你的诗。因此我抄了所有的诗,交给卡夫卡博士评价。”
“卡夫卡博士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他。”
“他是马克斯·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马克斯·布罗德的书《第谷·布拉赫走向上帝的路》就是献给他的。”
“那他就是《变形记》的作者!”我高喊起来,“这篇小说妙极了!你认识他?”
父亲点点头。“他在我们的法务部工作。”
“他对我写的东西怎么说?”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原想,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后来
他请我把你介绍给他。我跟他说了,你今天去。”
“这就是你说的去见人的事,是吧?”
“是的,就是去见他。”
父亲带我走到三楼,来到一间布置得很好的大办公室。房间里两张办公桌并排放在一起,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他一头黑发向后梳着,大鼻子,窄窄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微微苦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个孩子啦。”他说,连句问候也没有。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伸过手来。“在我面前您不用害羞。我也交一大笔电费。”他笑起来,我的胆怯消失了。
他就是神秘的甲虫萨姆沙的作者,我心中想道。我看见面前站的是个简朴的普通人,不禁有些失望。
“您的诗里还有许多喧闹,”父亲走出办公室后,弗朗茨·卡夫卡说,“这是青年人的并发症,他们生命力过于旺盛。甚至这种喧闹也是美的,虽然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喧闹妨碍表达。但我不是批评家。我不能很快变成什么,然后又很快回到我自身中,精确地测量距离。我已经说过,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
“不是法官?”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微微一笑。
“我虽然是法庭工作人员,但不熟悉法官。也许我只是个小小的法庭杂役。我没有什么明确固定的任务。”卡夫卡笑了。我跟他一起笑,虽然我不懂他的话。
“只有痛苦是确定的。”他严肃地说,“您在什么时候写作?”
我没有想到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道:“晚上,夜里。白天很少写。白天我不能写。”
“白天是个大魔术师。”
“光亮妨碍我写,工厂、房子、对面的窗户都妨碍我。最主要的是光,光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单独监禁的处境。”
难道他自己不也是《变形记》中的不幸的甲虫吗?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我很高兴,这时门开了,我父亲走了进来。
卡夫卡浓眉大眼,眼睛是灰色的。他褐色的脸生动活泼。他用表情传言。
只要能用脸部肌肉的运动代替话语,他就这样做。微笑,皱眉,蹙起前额,努嘴或撮尖嘴唇,这些都是他代替说话的动作。
弗朗茨·卡夫卡喜欢手势,因此他轻易不用手势。他的手不是伴随谈话的辅助手段,而仿佛是独立的动作语言的话语,是一种交际手段,绝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有目的的意念表达。
十指交叉,或手掌摊开放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上身舒适而又紧张地后靠在椅子上,脑袋前倾,双肩微耸,把手放在胸口——这就是他有节制地使用的表达手段的一小部分。他在做这些动作时总露出请求原谅的微笑,仿佛他要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做游戏,不过我希望,我的游戏能让你们喜欢。而且—而且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因公事认识的。”父亲回答,“我设计了卡片柜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做的模型。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下午下班后,会在卡林区波德布拉德街上的科恩霍伊泽木匠家‘干几个钟头’。从那时起我们就常谈
私事。后来我把你的诗给了他,我们就成了熟人。”
“为什么不是朋友?”
父亲摇摇头说:“要交朋友嘛,他太胆怯,太内向了。”
我第二次去看卡夫卡时问他:“您还到卡林的木匠家去吗?”
“这您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
“不去了,我早就不去了。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去。身体陛下不许。”
“这一点我能想象。在尘土飞扬的作坊里劳动不是什么舒服的事。”
“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劳动。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夜晚的到来总让我感到十分诧异。”
“晚上您一定很累。”
“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活,我也干过农活,莳弄过花草。那些活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工匠呢。”
“您把一切都留在这里?”
“为了到安全优美的地方找到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把一切留在这里。您知道作家保罗·阿德勒吗?”
“我只知道他的《魔笛》一书。”
“他在布拉格,和妻子儿女在一起。”
“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没有职业。他只有使命。他带着妻子儿女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他是个自由人,自由作家。在他身边,我总感到良心不安,我就这样让我的生命在办公室里窒息而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