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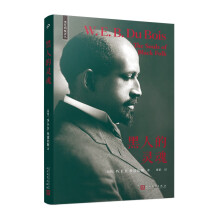






秋天的快乐
季节越是萧索,越是与我息息相关。白霜增加了往来的困难,乡下的居民于是独处一隅,因为离群索居让人感到更舒服。
秋天的景物关联着一种精神特征:树叶脱落仿佛我们的岁月,鲜花凋零仿佛我们的时刻,流云飞逝仿佛我们的幻想,光亮渐暗仿佛我们的智力,太阳变冷仿佛我们的爱情,河流冰封仿佛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和我们的命运有着隐秘的关系。
我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看着暴风雨的季节回来了,天鹅和野鸽飞走了,小嘴乌鸦又聚集在水池边的草地上,入夜时分栖止在宽阔的槌球场边最高的橡树之巅。当黄昏在林间升起近乎蓝色的水汽,当风在枯萎的青苔上悲叹或吟着小诗,种种与我性情相合的感觉就一齐涌上心头。要是我遇见了一个伫立在休闲的田头的农夫呢,我就停下脚步,端详起这个人,他在谷穗的掩映下出生,他也应在谷穗的掩映下死亡,他用犁铧翻动着坟墓的土,把滚烫的汗水滴进秋天冰冷的雨中:他挖出的沟正是他身后的纪念。对此,我的守护女神又能做什么呢?她用魔法将我带至尼罗河畔,指给我看掩埋于沙石之中的埃及的金字塔,一如阿里莫里克的犁沟有朝一日隐藏于欧石楠根下。我不禁庆幸已将有关我的至福的种种神话置于人事的圈外。
晚上,我独自登船,在池塘上穿行于灯芯草和睡莲的巨叶之间。那儿,准备离开我们这里的燕子已经会合,呢喃之声全都收入我的耳中——儿时的塔佛尼埃也不会对一位旅行者的记述这般全神贯注。落日中,这些燕子在水面上嬉戏,追逐昆虫,一齐冲上天空,像是考验它们的翅膀,然后又向湖面俯冲,接着就立于芦苇之上。芦苇只是微微弯了弯,而杂乱的叫声则响成一片。
概述我这一生中地球上的变化
我生活于两个世纪之交,仿佛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我扎进翻腾浑浊的水中,遗憾地远离我出生的旧岸,怀着希望向一个未知的岸游去。
我们古老的风俗中有一个说法:我从床上能看见天空了。从那时起,全部的地理都变了。如果我比较两个地球,一个是我生命之始的地球,一个是我生命之终的地球,那我就都认不出来了。陆地的第五个部分,澳大利亚,已经被发现,并且住上了人;第六块大陆也在南极的冰海中被法国的帆船望见;帕里、罗斯、富兰克林等人也已绕北极的海岸航行一周,画出了美洲的北缘;非洲开放了它神秘的孤独: 总之,我们的家园现在已没有一个角落还不被人知。人们学习地球上所有使世界分离的语言,人们大概会很快看到船只通过巴拿马地峡和苏伊士地峡。
历史也在时间的深处做出重大的发现,神圣的语言已让人读出它们湮没失传的语汇,商博良在麦兹拉依姆的花岗岩上破译了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仿佛盖在沙漠嘴唇上的封铅,回应着它们永恒的审慎……
船舶借助刚刚逝去的运动,不再局限于河上航行,穿越了大洋;距离缩短了;不再有急流,季风转换期,逆风,封锁,关闭的港口。从这些工业传奇到普朗库埃的茅草屋,距离何其遥远: 那时候,女人们在家里玩牌;农妇们纺麻织她们的衣裳;昏暗的树脂蜡烛照耀着乡村的夜晚;化学根本没有显示出它的奇迹;机器也没有使所有的水流和铁器动起来织毛线和绣丝绸;煤气还是个转瞬即逝的东西,根本不曾向我们的剧场和街道提供光明。
这些变化并未局限于我们的日常应用。人类出于追求永生的本能,将其智力向上伸展。他在苍穹每走一步,都承认了难以言明的力量的奇迹。那颗星,我们的父辈看来简单,我们看来却两倍三倍地复杂。阳光置于阳光的前面,就产生阴影,并且没有空间容纳其扩大。在无限的中央,天主看着这些壮丽的行列在他周围行进,这在最高存在的证据之上又增添了证据。我们用父亲家里的那两盏灯换取这些奇妙的东西。
让我们想象一下吧,根据变得强大的科学,我们这颗羸弱的行星游动在一个以阳光为波浪的海洋中,游动在这条银河之中,这条银河乃光的原材料,是造物主使之成形的万物的熔化了的金属。某星的距离如此神奇,其光到达望着它的眼睛之时,此星已经死灭,光源死灭于光线之前。人在其活动的原子中何等渺小,然而他作为智力又是何等伟大!他知道星辰的表面什么时候蒙上阴影,彗星数千年之后于哪个钟点返回,而他的生命仅为一瞬!他是天之袍的皱褶里的一个看不见的微小的虫子,然而星球在太空深处的每一步都瞒不过他。我们刚刚发现了这些星辰,那么,它们将照亮什么样的命运?这些星辰的发现和人类的某个新阶段有联系吗?你们会知道的,将要诞生的人;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退下。由于我的异乎寻常的高龄,我的纪念碑完成了。这对我是很大的宽慰。我觉得有人推我。我在船上订了座位,船老大通知我一会儿就要上船了。倘若我曾经是罗马的主人,我就要像苏拉那样说,我在我的死亡的前夕写完了我的《墓中回忆录》;但是我不会像他那样用这样的句子结束叙述:“我在梦中看见了我的一个孩子,他指给我看他的母亲梅黛拉,鼓励我到永恒幸福的怀抱里享受休息。”即便我曾经是苏拉,荣耀也永远不能带给我休息和幸福。
新的风暴即将形成,人们相信预感到了灾难,更甚于我们曾经饱尝过的痛苦。为了重返战场,人们已经考虑重新裹上旧日的伤口。然而我不认为不幸会在近期发生: 民众和国王都已筋疲力尽;意外的灾祸不会猛扑在法国身上,在我身后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全面变革的后果而已。无疑,人们将触及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视静止现象,世界不会没有痛苦就改变面貌(它必须改变)。但是,再来一下,并不就是另外的革命,那将是大革命趋向结束。明天的景象已与我无关,它呼唤着别的画家:该你们了,先生们。
1841年11月16日,我写下这最后的话,我的窗子开着,朝西对着外国使团的花园。现在是早晨六点钟,我看见苍白的、显得很大的月亮,它正俯身向着残老军人院的尖顶,那尖顶在东方初现的金色阳光中隐约可见,仿佛旧世界正在结束,新世界正在开始。我看得见晨曦的反光,然而我看不见太阳升起了。我还能做的只是在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后勇敢地下去,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恒。
秋天的快乐
季节越是萧索,越是与我息息相关。白霜增加了往来的困难,乡下的居民于是独处一隅,因为离群索居让人感到更舒服。
秋天的景物关联着一种精神特征:树叶脱落仿佛我们的岁月,鲜花凋零仿佛我们的时刻,流云飞逝仿佛我们的幻想,光亮渐暗仿佛我们的智力,太阳变冷仿佛我们的爱情,河流冰封仿佛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和我们的命运有着隐秘的关系。
我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看着暴风雨的季节回来了,天鹅和野鸽飞走了,小嘴乌鸦又聚集在水池边的草地上,入夜时分栖止在宽阔的槌球场边最高的橡树之巅。当黄昏在林间升起近乎蓝色的水汽,当风在枯萎的青苔上悲叹或吟着小诗,种种与我性情相合的感觉就一齐涌上心头。要是我遇见了一个伫立在休闲的田头的农夫呢,我就停下脚步,端详起这个人,他在谷穗的掩映下出生,他也应在谷穗的掩映下死亡,他用犁铧翻动着坟墓的土,把滚烫的汗水滴进秋天冰冷的雨中:他挖出的沟正是他身后的纪念。对此,我的守护女神又能做什么呢?她用魔法将我带至尼罗河畔,指给我看掩埋于沙石之中的埃及的金字塔,一如阿里莫里克的犁沟有朝一日隐藏于欧石楠根下。我不禁庆幸已将有关我的至福的种种神话置于人事的圈外。
晚上,我独自登船,在池塘上穿行于灯芯草和睡莲的巨叶之间。那儿,准备离开我们这里的燕子已经会合,呢喃之声全都收入我的耳中——儿时的塔佛尼埃也不会对一位旅行者的记述这般全神贯注。落日中,这些燕子在水面上嬉戏,追逐昆虫,一齐冲上天空,像是考验它们的翅膀,然后又向湖面俯冲,接着就立于芦苇之上。芦苇只是微微弯了弯,而杂乱的叫声则响成一片。
概述我这一生中地球上的变化
我生活于两个世纪之交,仿佛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我扎进翻腾浑浊的水中,遗憾地远离我出生的旧岸,怀着希望向一个未知的岸游去。
我们古老的风俗中有一个说法:我从床上能看见天空了。从那时起,全部的地理都变了。如果我比较两个地球,一个是我生命之始的地球,一个是我生命之终的地球,那我就都认不出来了。陆地的第五个部分,澳大利亚,已经被发现,并且住上了人;第六块大陆也在南极的冰海中被法国的帆船望见;帕里、罗斯、富兰克林等人也已绕北极的海岸航行一周,画出了美洲的北缘;非洲开放了它神秘的孤独: 总之,我们的家园现在已没有一个角落还不被人知。人们学习地球上所有使世界分离的语言,人们大概会很快看到船只通过巴拿马地峡和苏伊士地峡。
历史也在时间的深处做出重大的发现,神圣的语言已让人读出它们湮没失传的语汇,商博良在麦兹拉依姆的花岗岩上破译了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仿佛盖在沙漠嘴唇上的封铅,回应着它们永恒的审慎……
船舶借助刚刚逝去的运动,不再局限于河上航行,穿越了大洋;距离缩短了;不再有急流,季风转换期,逆风,封锁,关闭的港口。从这些工业传奇到普朗库埃的茅草屋,距离何其遥远: 那时候,女人们在家里玩牌;农妇们纺麻织她们的衣裳;昏暗的树脂蜡烛照耀着乡村的夜晚;化学根本没有显示出它的奇迹;机器也没有使所有的水流和铁器动起来织毛线和绣丝绸;煤气还是个转瞬即逝的东西,根本不曾向我们的剧场和街道提供光明。
这些变化并未局限于我们的日常应用。人类出于追求永生的本能,将其智力向上伸展。他在苍穹每走一步,都承认了难以言明的力量的奇迹。那颗星,我们的父辈看来简单,我们看来却两倍三倍地复杂。阳光置于阳光的前面,就产生阴影,并且没有空间容纳其扩大。在无限的中央,天主看着这些壮丽的行列在他周围行进,这在最高存在的证据之上又增添了证据。我们用父亲家里的那两盏灯换取这些奇妙的东西。
让我们想象一下吧,根据变得强大的科学,我们这颗羸弱的行星游动在一个以阳光为波浪的海洋中,游动在这条银河之中,这条银河乃光的原材料,是造物主使之成形的万物的熔化了的金属。某星的距离如此神奇,其光到达望着它的眼睛之时,此星已经死灭,光源死灭于光线之前。人在其活动的原子中何等渺小,然而他作为智力又是何等伟大!他知道星辰的表面什么时候蒙上阴影,彗星数千年之后于哪个钟点返回,而他的生命仅为一瞬!他是天之袍的皱褶里的一个看不见的微小的虫子,然而星球在太空深处的每一步都瞒不过他。我们刚刚发现了这些星辰,那么,它们将照亮什么样的命运?这些星辰的发现和人类的某个新阶段有联系吗?你们会知道的,将要诞生的人;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退下。由于我的异乎寻常的高龄,我的纪念碑完成了。这对我是很大的宽慰。我觉得有人推我。我在船上订了座位,船老大通知我一会儿就要上船了。倘若我曾经是罗马的主人,我就要像苏拉那样说,我在我的死亡的前夕写完了我的《墓中回忆录》;但是我不会像他那样用这样的句子结束叙述:“我在梦中看见了我的一个孩子,他指给我看他的母亲梅黛拉,鼓励我到永恒幸福的怀抱里享受休息。”即便我曾经是苏拉,荣耀也永远不能带给我休息和幸福。
新的风暴即将形成,人们相信预感到了灾难,更甚于我们曾经饱尝过的痛苦。为了重返战场,人们已经考虑重新裹上旧日的伤口。然而我不认为不幸会在近期发生: 民众和国王都已筋疲力尽;意外的灾祸不会猛扑在法国身上,在我身后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全面变革的后果而已。无疑,人们将触及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视静止现象,世界不会没有痛苦就改变面貌(它必须改变)。但是,再来一下,并不就是另外的革命,那将是大革命趋向结束。明天的景象已与我无关,它呼唤着别的画家:该你们了,先生们。
1841年11月16日,我写下这最后的话,我的窗子开着,朝西对着外国使团的花园。现在是早晨六点钟,我看见苍白的、显得很大的月亮,它正俯身向着残老军人院的尖顶,那尖顶在东方初现的金色阳光中隐约可见,仿佛旧世界正在结束,新世界正在开始。我看得见晨曦的反光,然而我看不见太阳升起了。我还能做的只是在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后勇敢地下去,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