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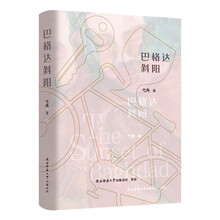




☆ 首部获得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非洲作家作品,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得主阿瓜卢萨引爆世界文坛的大师杰作;
☆ 阿瓜卢萨是当代安哥拉乃至整个葡语世界的代表作家,也是近年来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作品译为30多种语言出版,全球文学爱好者必读;
☆ 疯狂奇幻的想象力,博尔赫斯的灵魂转投蜥蜴肉身,穿行于梦和现实,具有神秘而明亮的热带气息;
房屋
这座房屋是活的,是有呼吸的。一整晚,我都能听见它的叹息。宽阔的墙壁由砖石和木材制成,总是凉凉的,即便是在正午,当阳光使得群鸟寂静,鞭笞着树木,融化了柏油路的时候。我沿着墙壁滑过,就像一只寄生在宿主皮肤上的蜱虫。倘若我抱住它,就能感受到一颗跳动的心脏。也许是我自己的。也许是房子的。都无关紧要。对我而言,一切都好。它给我带来了安全感。有时候,老埃斯佩兰萨会带来她最小的孙子。她背着他过来,用一块布紧紧裹住他,这是这片土地上的民间老法子。所有的活儿,她都这么做。清扫地板、掸去书本上的灰尘、打扫厨房、洗衣服,再用熨斗在上面熨过。那个小婴儿就把脑袋贴在她的背上,感受她的心跳和她的温度,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便睡去了。我与这间房子也有着相似的关系。我已经说过,黄昏时我会待在客厅,贴着玻璃窗,注视着太阳渐渐死去。等到夜幕降临,我则徜徉在不同的地方。客厅连通着庭院,它很狭小,而且疏于打理,唯一的魅力只在两株壮观的帝国棕榈树,非常高大,极为高傲地分别屹立在两端,把守着房屋。客厅也与书房相连,从书房到走廊之间要穿过一扇大门。走廊就是一条深深的隧道,又潮又暗,通向卧室、餐厅和厨房。房子这部分面向后院。碧绿柔和的晨光从鳄梨树高高的枝杈上滤过,轻抚着墙壁。在走廊尽头,就是从客厅走进来的左手边,有一道窄小的楼梯艰难地立在那里,台阶坏了三级。拾级而上,就会到达类似阁楼的地方,白化病人很少到那里去。里面满是装着书的盒子。我也不经常过去。有蝙蝠在墙上沉睡,从头到脚都裹在漆黑的斗篷里。我不知道蜥蜴在不在蝙蝠的菜单上。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了。同样的理由——恐惧阻止了我去后院探索。透过厨房、餐厅或是费利什房间的窗户,我看见杂草在玫瑰花丛中肆无忌惮地生长。一棵巨大的鳄梨树就矗立在院子正中央,枝繁叶茂。还有两棵高大的枇杷树,上面结着枇杷。还有十多棵木瓜树。费利什相信木瓜有再生的力量。一堵高墙将庭院围拢起来。墙顶上覆满了五颜六色的玻璃碎片,用水泥固定在那里。从我这里看去,像是一排獠牙。这样凶恶的手段也无法阻止男孩们时不时地跳过墙来偷鳄梨、枇杷和木瓜。他们在墙上放下一条木板,然后站起身来。我觉得,对这么一点收益而言,他们的行为太过火了。也许他们就不是为了品尝果子才这么做。我确信,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品尝风险。或许从此以后,他们总能从风险中尝到成熟的枇杷味。让我们想象一下,他们中的一个将来会成为一名工兵。这个国家不缺工兵的工作。就在昨天,我还看见电视上播出了一次扫雷行动进程的报道。一个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对数目的不确定性表示遗憾。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安哥拉的土地里埋了多少颗地雷。一千万到两千万。地雷有可能比安哥拉人还多。因此,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那些男孩中有一个成了工兵。每当他循迹穿过雷区,嘴里肯定都会出现一股久违的枇杷味。有一天他要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外国记者抛来的,混合了好奇与恐惧:“清除地雷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然后那个仍在他身体里面的男孩微笑着回答:“在想枇杷,先生。”
对这件事,老埃斯佩兰萨认为,正是墙壁引来了小偷。我听见她这么和费利什说。白化病人面向她,被逗乐了:“都想来这儿看看呢,我家里竟然有个无政府主义者?!等会儿我就会发现你正在读巴枯宁了。”
他说完,就没再注意她了。老埃斯佩兰萨从没读过巴枯宁,这是当然的;不仅如此,她从没读过任何一本书,她不识几个字。不过总的来说,我慢慢学到了许多有关生活的事,或者说,是有关在这个国家里的生活,在一个醉人的国家里的生活。她整理屋子时,我也听见她一个人自言自语,时而是轻柔地低语,好像谁在歌唱,时而声音又很大,好像谁在痛骂。老埃斯佩兰萨坚信自己永远不会死去。1992 年,她在一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当时她去了一位反对派领导人家里,取一封小儿子的信,他正在万博服役。突然,从四面八方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枪响。她坚持要离开那里,回她的穆塞克去,但其他人不让:“你疯了,女士,就假装正在下雨,一会儿就过去了。”
但没有过去。枪声像是一场暴风雨,变得愈加强烈、密集,而且开始向房屋这边靠近。费利什给我讲了那天下午发生的事:
“来了一支荒唐不堪的部队,是一群全副武装的暴徒,喝得酩酊大醉。他们闯进屋里,对所有人一顿毒打。指挥者想知道老妇人的名字。她对他说:‘埃斯佩兰萨·若布·萨帕拉洛,先生。’然后指挥官笑了。他嘲弄地说:‘埃斯佩兰萨会是最后一个死的。’暴徒让领导人和他的家人在院子里排成一列,然后向他们开枪射击。轮到老埃斯佩兰萨的时候,没子弹了。‘是后勤救了你一命。’指挥者冲她喊道,‘我们老是在后勤上出问题。’之后就命令她离开了。现在,她就觉得自己对死亡是免疫的。也许吧。”
我不觉得这不可能。埃斯佩兰萨·若布·萨帕拉洛的脸上有张皱纹织成的薄网,头发全白了,但肌肉还很紧实,姿态也总是坚定又精准。在我看来,她就是一根立柱,支撑着这栋房子。
小夜神
房屋
外国人
一艘满载声音的船
第一个梦
阿尔巴
若泽·布赫曼的诞生
第二个梦
光辉
一只蜥蜴的哲学
幻觉
我没有在第一次死亡中死去
第三个梦
风铃
第四个梦
我,欧拉利奥
童年的雨
在生活与书本之间
小世界
蝎子
部长
艰难岁月的果实
第五个梦
真实的角色
反··
无关紧要的人生
埃德蒙多·巴拉塔·多斯雷斯
爱情,一场犯罪
叶子花的呐喊
戴面具的人
第六个梦
费利什·文图拉开始写日记了
记忆、历史与重建中的国家——代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