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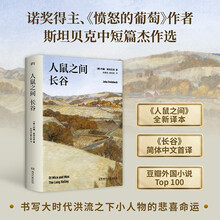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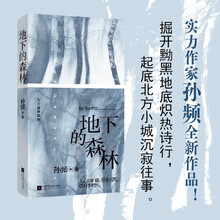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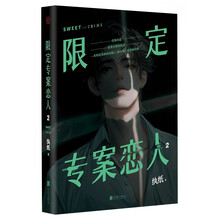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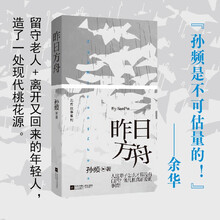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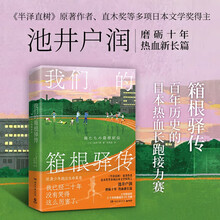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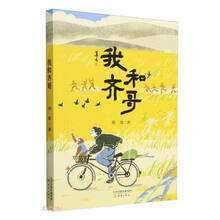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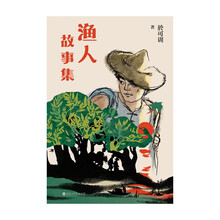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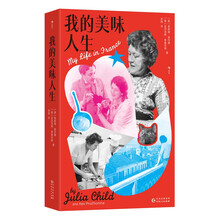
小说叙述语言有作者独特的个人风格,遣词造句朦胧而细腻,充满诗性,情感表达细腻,人物形象鲜明,戏曲唱词与情节故事形成互文,小说语言氛围和时代相契合,读者能够沉浸式地感受那个年代里,不同性格人物飘摇不定的戏曲人生。
本书是作家黄披星在长篇小说领域的首bu作品,以戏曲男旦远舟的跌宕人生为叙事线索,讲述了一个传统戏班在时代洪流中几经起伏,人们各奔西东而走向各自命运的故事。远舟从被人嘲笑到成为名噪一时的男旦,再到后来的自我放弃与坚守,小说通过描写他与周围人物的故事,刻画了戏班艺人群像,细腻地展现了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在艺术与现实冲突中的困惑、迷茫、坚守等心理变化。
“嗒咔铃嗒嚓啦……嗒,咔,铃,嗒,嚓啦……”这是戏班里打板练习的木鱼节奏,学员们都是用嘴来念的。无数次的练习后,远舟甚至连梦里也回响着这样的节奏。以前远舟觉得雨声最容易让自己入睡,现在是这木鱼声。他隐隐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进到了另外的一个场里,就像他看过的古戏《哪吒闹海》,他好像也在练习一种分身的法术。在那个场里,他仿佛走过了漫长的时间,如同戏曲中他练了很多年的蹀步——那是一种模仿古代女子行不动裙的走路方式,走得摇摇晃晃的,虽然也就几步路,却代表了很多的路,包括那些向上攀登的步伐。(第一部 戏船)
这些唱段,远舟倾尽全力,唱得情真入骨,足以让听的人汗毛尽竖。远舟也觉得这是自己这么些年唱戏,最尽心也最尽兴的一次。看那场面,村里人也似乎被他震住了,他几乎能听到场下每个人呼吸的节律,在跟随着自己的唱腔起起伏伏。这些年的经验,已经让远舟能够比较自如地把握观众的情感投入程度。他能看到场下的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芒,像是萤火般跳跃着的悲欢离合。
一曲终了,远舟看着村庄的天际,入夜的天空还有黝红的云彩在飘浮着,天际线上隐约还有几声闷雷在轰响。这个季节的雷,并不多见。“你唱好了,那人和神都能听见。”这话宛平师傅说过。那这算感动了天吗?他自己问自己,也觉得有趣。(第二部 静水无痕)
时间是有自己的折叠方式的。对齐云来说,时间几乎是在倒着行走的。她常常把自己的时间推到离开溪盘村之后,远舟伤心欲绝地唱着《珍珠衫》的时候。齐云为了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之门,在一种下意识的诱引下,选择了另一条路。她以为这是可以跟远舟并排行走的路。那是她原本向往的聚光灯下的独立角色,而不是被当作第三或第四角色那般可轻易被替换的角色。但她后来再想起的时候,总觉得那就是一种舍弃:看似舍弃了远舟,其实是舍弃了她自己——最初温婉的那一部分。当然,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不愿意屈服。
嫁给文生几乎是定数。从她离开溪盘开始,到她进工厂又出来再进文生弄的剧团,就基本上注定了这段姻缘。要说后悔也是有的,但她毅然决定重新走上舞台,这个婚事就已经在她预料之中了。她也不是说没再想起远舟,想起那些温热的年少时光,但她知道那已经回不去了——能回去就不是她自己了。那时候,她就是这么想的。为了舞台上的位置,为了那短暂却带着梦幻感的时刻——那种在舞台光影之下的眩晕感——她不顾一切。(第三部 百花亭)
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远舟觉得,这海上的行程,跟当年头几次坐着溪船去其他村社唱戏的过程,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令人心潮澎湃的旅程。这海洋深处,会不会停留着父亲当年的愿望?那条木兰溪,就曾经沉淀着远舟的无数心事——那些呼喊的声音,那些晃动的身影,从戏场的锣鼓到木鱼的肃穆……都在无声流淌着。
海上的行程并不漫长,但远舟还是想起了在溪船上过夜的情景。入夜的木兰溪是安详的,尤其是夏天,四周是影影绰绰的树影,也有些朦朦胧胧的身影。一船人都在的感觉,是安稳的、舒适的,也是劳累的和充满趣味的。而这海面上的行程,是壮阔的、热烈的,又是光芒四射的和纵情狂呼的。这不是去赴一场婉约的相遇,而是溯一场跨世纪的追寻。这也是相会,是前所未有的越洋之会。(第四部 目连)
001/引子
003/第一部 戏船
105/第二部 静水无痕
191/第三部 百花亭
295/第四部 目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