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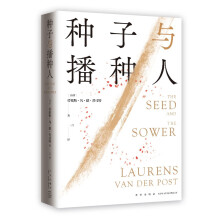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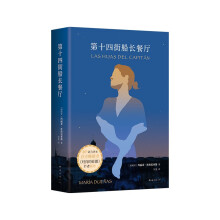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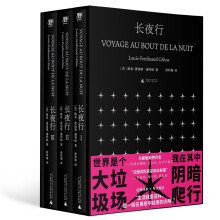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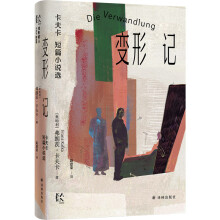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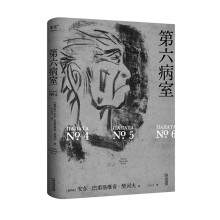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是我最喜欢的苏联文学作品之一。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最初知道这个春意盎然的名字是源于同名的苏联影视剧,苏联著名演员吉洪诺夫在剧中所扮演的施季里茨甚至影响了那一代的苏联人的人生选择。与影视作品相比,文学作品失去了许多演员个人魅力可以带来的观感享受,却在细节处给人更多的遐想空间,形形色色的正反人物的内心也更加舒展。正如导演程耳在看完《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后的感受:历史中的无名者开始有了轮廓。《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从题材来看,当属类型小说,它的故事也确实跌宕起伏,令人欲罢不能,但这部作品最da的魅力在于,它以全新的形式回归到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中来,它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关于善与恶的深刻思考。
1945年2月12日(6点38分)
“神父,您怎么看,在人的身上,是人性多点还是兽性更多呢?”
“我认为,在人身上,人性和兽性一样多。”
“这是不可能的。”
“可能,而且只能是这样的。”
“不是的。”
“不然的话,其中某一方早就取胜了。”
“您在责备我们,认为我们将精神置于次要的地位,就是热衷于鄙俗。精神确实是次要的。精神的成长只是犹如雨后之蘑菇,需要依赖合适的培养基。”
“那么,什么是合适的培养基呢?”
“功名利禄。就是你们所谓的淫欲,我称之为一种健康的愿望,就是想与一个女性睡觉并爱她的愿望。这是一种想掌控个人事物的健康的愿望。没有这些欲望和野心,人类的一切发展都将止步不前。教会不是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去阻止人类的发展嘛。您很清楚,我在讲教会的哪一个历史阶段吧?”
“是的,是的,我当然知道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不仅清楚地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我还知道其他阶段的所有历史。我是看不出来,在你们的人学知识和元首的宣传之间有什么差别。”
“是吗?”
“是的。他把人看作是功名利禄之徒。把人看成是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渴望为自己夺取生存空间的野心家。”
“您还没有意识到吧,您说的根本不对。因为元首不仅把每个德国人看成是一个有抱负的家伙,而且,这还是一群浅色头发的高等人类。”
“而您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抽象的野心家。”
“我是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了他的起源。人是由猴子变来的。而猴子本身不就是动物嘛。”
“在这一点上,我和您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您相信,人的起源是从猴子变来的;可是您并没有见过那只变成了人的猴子,这只猴子也从没有在您的耳边就这个论题和您讨论过什么。您没有对这个问题深入地研究过,您也不可能去探索这样一个问题。您对此深信不疑,只是因为这种信仰与您的精神世界保持一致罢了。”
“难道上帝就曾经在您的耳边告知您,说是他创造了人吗?”
“当然,谁也没有这样对我说过这种事,而且,我也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无法证明的,对此种事物,只能去相信。您相信猴子,而我,相信上帝。您相信猴子,因为这种信仰与您的精神世界相吻合;我信仰上帝,因为这种信仰与我的精神世界相吻合。”
“您在极力歪曲事实。我不是相信猴子,我是相信人。”
“您相信从猴子变来的人。您是相信人身上的猴子。而我,相信人身上的上帝。”
“怎么,难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吗?”
“那是当然。”
“在元首身上有吗?在戈林身上有吗?在希姆莱身上也有?”
“您提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我和您谈论的只是人的天性。当然啦,在每一个这类的坏蛋身上都可以发现堕落天使的痕迹。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天性已经受到残酷、专横、谎言、下流、强权的法则所支配,实际上,在他们的天性中,人性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原则上,我从不相信,人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必须承受起他源于猴子的这个诅咒。”
“为什么起源于猴子是一种‘诅咒’?”
“我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
“也就是说,有必要接受上帝的律法来消灭猴子喽?”
“为什么呢?没这个必要吧……”
“您一直在道义上回避对我的问题给出答案,这些问题使我深受折磨。您不给出‘是’与‘否’的回答,每一个寻求信仰的人,都是喜欢听到具体性的答案的,这样的人喜欢的是一个‘是’或者‘否’的回答。而从您的口中得到的总是‘不是吧’,‘不是吗’,‘可能不是吧’和其它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莫衷一是的字眼。如果这是您的意愿,那么我不仅会深深地讨厌您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更厌恶您的这一套说辞。”
“您对我的所作所为怀有敌意。这毫无疑问……您却还是从集中营跑到我跟前来聊个不停。这您又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这只是再一次证明了,正如您所说的,在人的身上既有上帝的神性,也有猴子的兽性。如果我的身上只有上帝的神性,我也就不会来求教于您。我也就不会逃避,而是会坦然地死在党卫队刽子手的枪口之下,将我的另一面脸颊转向他们,以唤醒他们中的哪怕一个人。现在,要是您不得不落到他们的手里,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会转过自己的另一面脸颊或者是不是极力避免被扇上一巴掌呢?”
“什么意思——这只是转过另一面脸颊的问题吗?您又把象征性的寓言投射在真实的纳粹国家机器上了。把转过另一面脸颊变成寓言是一回事。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是有关人类良知的寓言。而落入到并不征求您的意见、就要打另一面脸颊的机构中,则是另一回事。落入到原则上和思想上都丧失了任何良知的国家机器中……当然,这与在路上和车辆或者是石头相撞,或者是撞上了墙壁一样,和这样的顽固的东西是没什么可交流的,这和与其他物种交流一样是不可能的。”
“神父,我很抱歉,——也许,我触碰到了您的秘密,但……您是不是也进过盖世太保的监狱呢?”
“好吧,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是进过那里……”
“我懂了。您不想提及这段历史,因为这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问题。神父,您是否想过,战争结束之后,您教区的教民有可能不再相信您?”
“进过盖世太保监狱的人不在少数。”
“要是有人暗中告诉教民们,说神父您是告密奸细,和您同一个监牢的其他人都没有幸免,没有活着出来;而像您这样,能活着回来的人不过万分之几……教民们都不太相信您了……到那时候,您还向谁传教布道呢?”
“当然,如果用类似的方法去整人,完全能够置人于死地。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改变自己的处境。”
“到那个时候可怎么办呢?”
“到那个时候?这种说法就会被驳斥。我会尽我所能驳斥这种鬼话,直到他们愿意听我辟谣。要是他们不听我辟谣——我就是内心死亡了。”
“心死。就是说,您将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的躯壳?”
“听凭上帝的审判。躯壳就躯壳吧。”
“您的宗教反对自杀吧?”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会自杀了却此生。”
“没有了传教布道的可能,您会做什么呢?”
“我会不传教而信教。”
“难道您就看不到自己还有其他的出路吗?——譬如和大家一起劳作。”
“您所谓的‘劳作’指什么?”
“至少——搬运石头来建造科学的殿堂。”
“如果社会需要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人来搬运石头,那么我和您也就真的无话可说。这样一来,对我来说,实际上最好是现在就回到集中营里,在那里的焚尸炉里被烧掉……”
“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发生呢?我很想听听您的推测性的意见——这么说吧,这可以调整您的思路。”
“您认为,一个向自己的教民传教布道的人会是游手好闲、招摇撞骗的家伙吗?您不认为传教布道这是一种工作吗?您认为,搬运石头是一种工作,而我则认为,精神劳动和任何一种其他劳动都是平等的——精神工作尤其重要。”
“我本人是一名专业记者,我的通讯报道既遭到了纳粹的排斥,又被东正教教会所反对。”
“东正教教会方面的斥责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您对人本身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我并不研究抽象的人。我只不过报道了不来梅和汉堡那些贫民窟中小偷和娼妓的世界而已。希特勒的国家就斥责这种报道是对上等种族的卑鄙诽谤,而教会则称这种报道是对人的污蔑。”
“我们是不惧怕揭示生活中的真相的。”
“你们当然害怕!我只是展示了这些人只是想去教堂,而教堂极力将他们拒之门外;正是那些教民回避他们,于是神父也不敢去反对自己的教民。”
“当然不能那么做。我不会反对您报道真相。我不是因您将这一切报道出来而指责您。我和您的主要分歧在于对人的未来的预测。”
“您不觉得您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更像是政治家,而不像是一名神父吗?”
“您这样认为是因为您在我的身上只看到了适合您的那些东西,您身上也有的东西。您只看到了一个政治的轮廓,它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就像是在一个对数计算尺上能看出钉钉子的痕迹一样。对数计算尺确实可以用来钉钉子,它既有一定的长度,又有那么一点重量。但是,这样的观察方式你只能看到事物的第十种、第二十种功能,而实际上,借助于对数计算尺要做的事是计算,而不仅仅是钉钉子。”
“神父,我提了一个问题,而您没有回答,就把钉子钉在了我身上。您倒是非常巧妙地把我从一个提问者变成了回答问题的人。您轻巧地把我从一个探索者变成了异端人士。当您说您也在信仰追寻者之列的时候,为什么您能超脱于对这种信仰的纠结?”
“的确是这样的:我也在搏杀之中,我确实处于战争中,但我是在和战争本身作战。”
“您的论辩具有唯物论的特点。”
“我是在和一个唯物论主义者争辩。”
“就是说,您是在用我的武器和我论战?”
“我这么做是被迫的。”
“您听好了……为了神父您的教民安好——我需要您与我的朋友们取得联系。地址嘛我会给您。我信任您才给您我的同志们的地址……神父,我相信您不会出卖无辜的同志们……”
施季里茨听完这段磁带录音,立即起身走到窗前,他不想与来客的目光对视,他就是昨天求助于神父的那个人,现在这个人正喝着白兰地,贪婪地吸着烟,咧着嘴得意洋洋地笑着。
“神父那里没有烟可抽吧?”施季里茨头也没回地问道。
他站在占据了整个墙面的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乌鸦们在雪地上争抢着啄食面包屑:别墅的门卫领取的是双份口粮,又特别喜欢给鸟类投食。门卫不知道,施季里茨是党卫队保安局的人,他坚信,这所房子要么属于一群同性恋者,要么就是贸易大亨的谈事地点: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出入这里,男人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总是在房子里安静地谈话,吃的食物相当美味,都是上等货,喝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美国的。
“是的,我在那里可没有烟抽,受尽了折磨……那个老头子倒是很健谈,但是我因为没有烟抽烦躁得只想上吊……”
这个特工的名字叫克劳斯。他是两年前被招募的。他是本人自愿来参加征招的:这位前校对员太希望生活有点刺激了。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特别善于用真诚和鞭辟入里的见识让交谈者无从辩解,解除了交谈者的戒备之心。只要他的工作富有成效和节奏足够快,人们就会对他无所不谈。施季里茨注视着克劳斯,那种每天和他见面时越来越沉重的恐惧感再度浮现在心头。
“也许,他这也是一种病态?”施季里茨曾经这样想过,“对背叛的渴望也是一种疾病。有意思的是:克劳斯完全不符合隆布罗佐[ 切扎列·隆布罗佐(1835—1909):意大利都灵的犯罪心理学家,资产阶级刑法学中人类学派创始人。——作者注;本书指隆布罗佐创立了异常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理论以及犯罪博物馆,他的理论认为,有一种人因生理(低下)的原因,是天生的罪犯。]的理论——他比我所见过的所有罪犯都更危险和可怕,但是,他仪表堂堂,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施季里茨回到桌旁,坐到克劳斯的对面,含笑望着他。
“怎么样?”他问道,“就是说,您已经确信,这个老头子会为您建立起联系了?”
“是的,这已经是一个解决了的问题。我最喜欢和知识分子以及神父打交道啦。您知道,观察一个人一步步地走向死亡,这太让人心旌神摇了。有时候我太想说一句不适当的话了:‘站住!蠢蛋!知不知道你是往哪里走?!’”
“哎,这可没必要,”施季里茨说,“说这样的话未免太不理智了。”
“您这里有没有鱼罐头哇?吃不到鱼我可要馋疯了。您知道吧,鱼里含有磷。神经细胞需要磷……”
“我热几个上好的鱼罐头给您。您要吃哪种罐头呢?”
“我喜欢吃油煎的……”
“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您想吃哪国产的罐头?国产的还是……”
“就来那种‘还是’吧,”克劳斯笑着说,“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怎么爱国,但我最喜欢的食品和饮料都是美国或者法国生产的……”
“好哇,我会给您热一盒真正的法国沙丁鱼罐头。是橄榄油煎的,香味扑鼻,口齿生津,富含磷脂……是这样,我昨天看了你的专案材料……”
“要是能让我本人看上一眼,付出多高昂的代价我也愿意哦……”
“这些材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趣……当您侃侃而谈,笑声朗朗,述说您的肝部如何疼痛、不适——这些倒是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考虑到在此之前,您已经完成了一次相当惊险的行动的话……您那专案材料中的一切就相当的枯燥和乏味了:无非就是汇报材料啦、告密材料啦这些。您写的汇报材料和告发您的材料都混在一起啦……没意思,这些都没什么意思……倒是一些别的东西还有点意思:我统计了一下您的汇报材料,由于您的告密行动一共有97人被捕……而且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没有揭发您。毫无例外。他们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可是被整得够惨……”
“您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不知道……嗯,也许我想分析一下……当那些给您庇护的人被抓走时,您是不是也有过心痛的感觉呢?”
“您以为会如何呢?”
“我不知道。”
“只有鬼才知道……看来,我和他们一对一对谈或者对决的时候,总是感到自己是一个强者。我喜欢这种缠斗和搏杀……至于他们以后会有什么命运嘛,——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以后的命运会怎样呢?所有人的命运以后又会怎样呢?”
“这话没错儿。”施季里茨表示同意。
“我们死后,哪怕就是洪水滔天也与我们无关[ 据传这是法国的蓬巴杜夫人对国王路易十五说过的一句话,被享乐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
]。再看一看咱们这里都是一些什么人吧:到处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卑鄙无耻之徒、揭发告密的小人。人人莫不如此,毫无任何的例外。生在奴隶之中就当不成自由人……这话一点不错。不过,在奴隶之中选择做一个最自由的人不是更好些吗?我本人呢,这些年就享受了充分的精神自由……”
施季里茨问他:
“我说,前天晚上有人去找过神父吗?”
“没有人呀……”
“快九点钟的时候……”
“您可能弄错了,”克劳斯说,“至少,没有您这里派过去的人,在那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也许,是本区的教民?我的人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您在监视那栋房子?”
“当然。一直在监视呢……这么说,对这老头子会为我们工作这件事,您是坚信不疑喽?”
“他一定会为我们工作。我一向认为自己有当反对党党魁和宣传家的天赋,是个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领袖材料。人们总是在我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严密的思维逻辑之下臣服……”
“好哇。克劳斯,干得相当不错。只是别跟别人吹牛……现在我们谈谈案件……您这几天先在我们控制的安全地点呆上几天……这之后还有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要由您来做,而且实际上,这项工作并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施季里茨说的是实话。就在今天,盖世太保总部的同僚向他提出借用克劳斯一周的时间:两名俄罗斯的“钢琴师”在科隆被抓了。他们就是正在无线电发报机旁收发电报的时候,被当场擒获。他们拒不交代,这就需要在他们身边安插一个在这方面干起来得心应手的人。找不到比克劳斯更合适的人选啦。施季里茨允诺找到克劳斯。
“请您从灰色的文件夹里拿一张纸,”施季里茨说道,“写下以下内容:旗队长!我已经疲惫不堪,筋疲力尽。我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是,我再也受不了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了。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写这些话干什么呀?”
“我认为,这样写的话,您去因斯布鲁克休息一周就顺理成章了。”施季里茨一边回答他,一边将一沓钞票递给克劳斯。“那里的赌场都开门,年轻貌美的女士们正在滑雪下山。不手写这几句话,我怎么来为您开启一个星期的幸福之旅呢。”
“太感谢了!不过,我还有挺多钱呢……”
“钱越多越好嘛,是吧?难不成钱多还咬手?”
“这倒是的,钱多不咬手。”克劳斯同意道,接过钱,随手揣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据说,治淋病的话很贵,要花上一大笔钱的……”
“您再回忆一下:没有人见到过您去神父那里吗?”
“不用费力去想啦——真的没人看见……”
“我指的是有没有我们的人看见您。”
“要是您的人真的在监视那所房子,他们说不定也可能看见过我。但是呢,也未必……我反正是谁也没见到过……”
施季里茨想起了一周前他“导演”的一出“戏”,是他亲自给克劳斯穿上了囚犯的衣服,押着一队囚犯穿过了施拉格神父现在所住的村子。他回忆起了克劳斯一周前的样子,他那张脸上的表情: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一副和善而坚毅的脸庞——他当时已经进入了他所要扮演的角色之中。那时候,施季里茨和他说话是另外一副腔调,因为当时汽车里坐着的可是一位正人君子——看起来心慈面善,嗓音低沉,说出的话准确、中肯、无误。
“我们再去您的新住处的路上把这封信投到邮筒里,”施季里茨说,“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再寄一封信给神父。您亲自来写这封信吧。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去给您再煮一杯咖啡。”
当施季里茨回到桌旁的时候,克劳斯手里拿着写好的一页纸。
“诚实意味着行动,”克劳斯一边笑,一边读,“信仰基于斗争。完全无所作为地宣讲抽象的诚实是对教民和自己的背叛:一个人可以原谅自己的不诚实,而子孙后代却绝不会宽恕。所以,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无所作为。无所作为比背叛更为有害。我要走了。请您好自为之,上帝会保佑您的。”
“怎么样?还行吧?”
“太好啦。您从来没有想过写点小说什么的吗?或者试着写点诗呢?”
“没有。如果我要能写作的话,我又何必当……”克劳斯突然欲言又止,偷偷瞥了一眼施季里茨。
“继续说下去呀,您真是个怪人。我们谈什么都是开诚布公的。您是不是想说: 假如您要是会写作的话,就不会为我们工作了,是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不是差不多,”施季里茨纠正他的话,“您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吗?”
“是的。”
“您对我半吞半吐的原因是什么呀?喝完这杯威士忌,咱们就动身吧。天已经黑下来了,大概美国人很快就会开始轰炸了。”
“新的住处很远吗?”
“在林子里,距离这里有十公里左右。那里相当安静,您可以一觉睡到明天……”
已经坐在汽车里了,施季里茨又问道:
“他一句也没提起过前首相布吕宁[ 海因里希·布吕宁(1885—1970):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政治家,首相。]吗?”
“我已经和您汇报过这件事了,我一谈到这个人,他马上就绝口不谈了。我没敢使劲逼迫他说……”
“您做得很对……他也从没提起过瑞士吗?”
“一丝口风都没漏。”
“好吧。那我们再从别的途径寻求突破。重要的是,他已经同意帮助一名共产党员了。这个神父,可真有一套啊。”
施季里茨对着克劳斯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打死了他。他们那时是站在湖岸上。虽然说,这个地方是禁区,但是,施季里茨清楚地了解,它的警卫岗哨位于两公里之外,美国人的轰炸机已经飞过来了,在轰炸机的巨大轰鸣声中,手枪的射击声是不可能被听到的。他准确测量过,克劳斯会从水泥墩倒下去,这个地方以前是钓鱼者的站位,会一下子落入水中。
克劳斯无声无息地落入了水中。施季里茨把手枪也扔到克劳斯落水的同一地点(为了让由于神经极度衰弱而自杀的说法具有真实的可信度,信件都是克劳斯本人所写并寄出去的),他摘下手套,穿过一片森林,回到自己的汽车上。这里距离神父施拉格所住的村庄还有四十公里。施季里茨计算好了,自己到达那里还需要一个小时,他提前周密地考虑好了一切,甚至包括从时间上证明他不在现场的可能性……
“君乃何方神圣?”001
“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任务)030
排兵布阵089
信任的限度176
在伯尔尼是否一切准备就绪?239
大水冲了龙王庙?290
几分钟的节奏342
不合逻辑的逻辑359
良好的意图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