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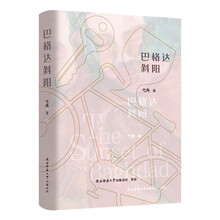




◆向被伤害的人伸出的援手,也是曾被他人紧紧握住的手。
◆受过伤的人,能更敏锐地感知他人的伤痛。弱者对弱者的微小善意,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光。
◆申东晔文学奖、大山文学奖、李孝石文学奖等多项大奖获得者、韩国著名作家赵海珍,金万重文学奖、大山文学奖获奖作品首度引进!
◆谁说底层只能互害,受过苦的人,才懂得他人的苦。普通人举手之劳的善意,会引发改变别人一生的蝴蝶效应!
◆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孩子,却也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珍视的孩子;不求回报的单纯的真心,点亮一个又一个崭新的生命!
◆温柔、美丽的文字,一个寻找自己名字意义的女孩;陌生人之间的互助与爱,是这个冬天zui温暖人心的治愈故事!
我来自黑暗。
囿于“永恒”这一无形框架,时间停滞不前的黑暗,也许就是我的根源。我没有方向,不知要去往何方,独自在那里游荡。那时的我,是一粒圆实的种子,还是一缕细长绵延的稀薄烟雾?也许是一种即便一个小小的反作用力也会使其轻易坍塌或消散的多变物质,或是一股无形的能量。
我形成于黑暗,冲破黑暗而生,所以我没有父母,也没有记得我成形时的胎梦、记住我呱呱坠地时的啼哭声并讲给我听的父母的父母,亦没有用相机记录下我会爬、会坐、会站、会说话时的亲戚和邻居。另外,记录父母个人信息的户口本、记录我出生日期的出生证明,以及我出生医院开具的病历表等,我同样没有。我有的,是为使领养事宜顺利进行而加急开具的独立户籍证明、代理人领养同意书、国际预防接种证明、旅行许可证明、为养父母提供翻译及各种便利服务的协调费申请书,以及领养服务中介费——若身体有残障,还可以得到优惠,对我这样的健康儿童,费用是固定的——此类收据可能保存在韩国的领养机构或管理领养机构的政府下属机关里。
我也有过脐带吗?偶尔产生这样的疑问时,我就会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肚子上,轻轻地抚摸肚脐周围。然而,肚脐只是亲生母亲留下的痕迹,连她的一根手指我都无法再现。毫无效力的证据、没有特性的符号、已封闭的通道……我不知道她的长相和给人的印象、体香和触感、说话时的语气和声音,也不清楚她微笑和哭泣时的表情、睡眠习惯和忌讳,今后也无从知晓。
对我来说,她是另一个黑暗。
今年六月,我又想起了久违的她。
那天,我躺在巴黎市内一家小型妇产科医院的病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超声波仪器屏幕上出现的细微动作,盯得眼睛都疼了。画面上,推测为头部、躯干和四肢的几个团块连在一起,有机地蠕动着。一位自称朱维特的白发医生向我道贺,告诉我这个新生命在我身体内已经孕育快九周了。
医生说:“知道吗?在短短二百八十天的时间里,受精卵会经历数十亿年的生命进化历程。单细胞受精卵通过不断分化,经过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进化成哺乳动物,再进化为生物学意义上最为复杂的哺乳动物——人类。现在是第九周,再过三周左右,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生殖器官)都会成形。总之,现在是泥土被捏制成人的阶段,得多加小心。”
就是这一瞬间我想起了她,虽然什么都想不起来但还是想了。这种“想”转而变成马上想要见到的渴望。这种有着陌生质感的渴望,竟然大而圆实,还很细腻。在这之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渴望,却依然想要了解她,想去寻找她,这让我不知所措。
走出医院,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附近的散步道走了一会儿。散着步,内心将两种可能的选择放在假想的天平两端,极力准确地拓展自己的思维。阳光透过头顶的树叶,像一张由光线织成的大网呈放射状洒落下来。我停下脚步,用力抬起头,仰望着随风摇曳的树叶。高大的林荫树成排伫立,一片片叶子紧密交织在一起,撑起一片绿色的凉荫,像是在保护我这个孕育着新生命的存在。树木伸向天空,天空的尽头应该连着宇宙。
宇宙……
“宇—宙—”,我又用韩语轻念了一遍。那一刻,之前所有的困惑都消失不见,只有“宇宙”这个名字留在心间。这名字法国人读起来不是很难,而且,如果是拥抱万物的宇宙的话,可以说这与无形的黑暗在意义上相去甚远。没有必要烦恼。不,烦恼已经结束了。我身体里的小生命,用他成形不久的柔弱心脏促进着血液循环,不停地增加细胞数量,以奇迹般的速度经历着进化过程,我自然而然地给他起了“宇宙”这个名字。应该记住这一刻,我想。记住这一刻风的方向、树叶的颜色,以及瞬息万变的云的形状。等宇宙以后学会了语言,关于这一刻,我会给他讲一个长长的故事。从现在开始,我要记住宇宙的每一刻。我既是连接宇宙与世界的媒介,也是向世人告知其存在的使者,还是他成长过程的见证人。我不会放弃这些角色,也绝不会让宇宙陷入哪怕片刻关于黑暗的想象。那天,在散步道边的大树下,唯有这一点成了我生命中的确定因素。
在得知宇宙到来的那天,我又收到一封自称“曙瑛”的韩国女性发来的电子邮件。
傍晚时分,我回到公寓,像往常一样靠在沙发上打开笔记本电脑,登录电子邮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曙瑛”这个名字。第一次收到曙瑛的邮件是在一周前。在第一封邮件中,她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女,今年二十九岁,自大学攻读电影专业以来,跟朋友们一起制作过多部独立电影;现在正构思制作一部纪录片式电影,想以我为主人公,讲述一个被领养到法国的韩裔戏剧演员兼剧作家的故事。当时她这么写道:
一年前,我读到一篇采访娜娜女士的文章。那时,我偶然从在我们公寓一楼经营餐馆的老奶奶那里听说,她年轻时曾临时照顾过一个即将被送养到国外的孩子。这不禁让我回顾了一下人生:我的人生中似乎不存在“领养”和“被领养”这种概念。也许正因如此,娜娜女士的故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苦思冥想,一部关于娜娜女士的电影终于构思出来了。
通过走访娜娜女士被领养到法国之前在韩国生活的地方,在那里接触过的人,最终了解娜娜女士的曾用名“문주”的含义。我现在所构思的电影就是想记录这一寻找过程。您也知道,韩国人的名字里包含着以符号和发音难以推断的固有含义。因此,娜娜女士,今天在此慎重地征询您的意见,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在韩国制作一部电影?
当时,我认为这个提议一点都不现实。为了出演一部作品价值毫无保障的业余导演拍摄的电影,暂时放弃目前巴黎的生活去韩国,这就像一个注定会失败的游戏,看上去很不明智。虽然当时感觉十分可笑,但我还是经常想起那封邮件。几天后我给那位极有魄力的年轻女导演回了邮件,只写了一行字:“您为什么偏偏对我这样一个被领养人的名字感兴趣呢?”她的第二封邮件应该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吧。
曙瑛所读到的,是我一年前接受的采访。当时韩国某民间团体专门为被领养到海外的韩裔人士举办了一场活动,我因此回到了阔别三十四年的韩国。据说,那次活动是在政府的资助下举办的,目的是为被领养人寻找在韩国的家人,并促成彼此见面。
在受邀的十五名被领养人中,我被采访,大概是因为在为期两周的活动进行到一半时,只有我还没找到家人吧。再加上和其他被领养人相比,我的韩语更流利些——我在法国也经常接触韩语,韩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没有太大问题。在我小时候,亨利和丽莎给我买了些韩国制作的童话书和动漫DVD。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意识地在网上找韩国电视节目或电影来看。上大学时,我和同校建筑专业一个名叫基贤的韩国留学生参加了语言交流活动,互相学习了将近四年。当时基贤建议说,要想掌握高级韩语,就要懂汉字。于是,有一段时间,我还自学了从二手书店里买来的汉字教材。
八月第二周的星期二,在首尔光化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二楼,我接受了约一个小时的采访。我尽可能详细地说明了被领养前后的情况。铁路、救我的火车司机、对他的印象和他的大概年龄、我被叫作“문주”时生活了一年的司机师傅家的氛围,以及我后来入住的孤儿院的名字……最后我从包里拿出三十四年前飞往法国时办理的、珍藏至今的一次性护照,翻开贴着照片的那一页给记者看。护照是在被领养前匆忙办理的,如果有人还记得我,我希望告诉那人关于我的所有信息,于是就带去了。正在认真敲击键盘的记者,突然抬起头看了看我,笑着说道:
“除了这些,想必您还有好多话要说吧……想请您谈一下法国的生活,以及久别故国再次回来的感受。”
我怔怔地望着记者。那位记者肯定猜不出我是抱着最后赌一把的心态接受的这次采访,这一点我明明知道,却依然有一股难以抑制的伤感瞬间涌上心头,也许这是一种近乎敌意的伤感。
采访结束后,记者称还有其他事情,先离开了咖啡厅。
那天,直到太阳下山,深夜降临,我一直静静地坐在咖啡厅里。玻璃窗外,光化门广场上的一顶顶帐篷也逐渐被黑夜晕染。在法国时看过相关新闻,所以我知道那些帐篷的存在,为的是不忘却一些人。看到新闻的那天晚上,外面下起了雨,我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身上的寒气依然没有消退。想起那个晚上,我感到更加孤独了。一个从遇难船上幸存下来,却无人前来营救,只能四处漂泊的人,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演绎我的孤独。把某一情景装饰成舞台,把我的孤独转移给那个想象中的演员,这已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习惯。我很喜欢那种被转移的孤独既属于我,但又不属于我,从而无须深陷其中的感觉。
杂志上刊登的那篇采访报道,我只读过一遍。是在收到邮寄的杂志后读的,而且在我离开韩国之前杂志就已出刊。不出所料,比起我被领养前的信息,杂志侧重介绍了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共有三页。当时,我刚获得法国某文化财团授予的戏剧奖,这段履历也被大篇幅报道,而我拜托刊登的护照照片并不在版面上。看到自己在光化门咖啡厅里拍的照片,我感觉不可能会有人认出我就是那个被遗弃在铁路上、曾被叫作“문주”的孩子。我最后所押的赌注,只是为了找到给我起“문주”这个名字的人,以及我的亲生母亲,而迄今为止他们未曾联系过我。
我凝视电脑屏幕许久,选中曙瑛的邮件,按下了删除键。我不认识曙瑛,也不了解她思考“문주”的时间,也就是她某天偶然间看到时事杂志上刊登的关于我的访谈报道,于是发挥想象,构思出一部电影的时间。那时间的形质与密度,对我来说都属于未知的领域。
我本想关上电脑,手却没有动。“不必太过敏感。”我对自己说。等看完曙瑛的回复后,再永久删除也无妨。于是我再次登录邮箱,恢复了刚刚删除的邮件,慢慢地读起她写的每一句话。
现在偶尔也会想,如果那时我没有恢复曙瑛的邮件,也没有参与曙瑛策划的电影,那么我的生活,就不会跟在韩国认识的任何人有交集。而那样的生活,就像缺少了最重要一页的书籍一样,无比空虚,简直无法想象……无论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都无法再回到遇见他们之前的过去了。
“因为名字是家。”
曙瑛的第二封邮件是这样开始的。
“名字是我们的认同感和存在感居住的家。在这里,一切都被遗忘得太快,我相信哪怕只记住一个名字,也是对消逝的世界的一种敬意。”
“认同感”“存在感”“家”“敬意”……曙瑛选择的词汇一下子便吸引住了我。不,“吸引”这个表达还不够恰当,那些词语正是我的人生所殷切期盼的。我不自觉地在沙发上坐直,聚精会神地读起邮件来。
曙瑛的策划似乎已有很大进展。电影的梗概已经构思好,连续镜头的顺序也已排好,制作人员亦已确定,而且已经跟在影视专业方面小有名气的母校打好了招呼,可以借到最新型的摄像机和镜头。虽然不能为我提供机票,片酬也不丰厚,但在拍摄的两三个月里,曙瑛可以为我解决住宿问题,她还附上了几张照片。我打开附件里的图片,小巧的客厅、卧室,以及窗外风景的照片,一一呈现在电脑屏幕上。曙瑛接着写道:“其实这是我自己住的房子,虽然不太高档,但一个人住没什么大问题,而且晚上还可以欣赏到灯火通明的南山塔。”
在我静静查看那些照片的时候,脑海中依稀浮现出对我来说相当于托管家庭的司机师傅的家。那个家在一个胡同里,是一处老式韩屋。一到下雨天,渗透到每个角落里的木头的香味,像薄荷香一样扑鼻而来。在那个家里,下雨也就意味着可以吃到一种褐紫色的扁平饺子状食物。尽管司机师傅的母亲平时一看见我就会不断咂舌,但当我们并排坐在开阔的地板上,听着雨声分享那种饺子状食物时,我会感觉她就像亲奶奶一样和蔼可亲。我已经记不清那种食物的名称了,只记得是在面团里放入磨碎的红豆,用油煎炸后,在上面轻撒些白糖制作而成。连名字都不记得了,我离开韩国后再也没有见过,但从几天前起,这个味道却开始在舌尖萦绕。如果能吃到这种在法国无法找到的食物,那么时时刻刻折磨我的恶心症状似乎马上就能缓解。当然我知道,只是为了吃一种食物而在怀孕初期长时间飞行,是一种不合常理的选择。我也知道,医生说过,这期间凡事都要小心。那时候我应该删除曙瑛的邮件,或是回信婉言谢绝,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想起以前在介绍韩国文化的宣传册里读到的内容——在韩国,许多孕妇会回娘家待一段时间来补充营养待产——内心开始有些动摇。最重要的是,通过曙瑛的电影,说不定可以找到司机师傅和他的母亲!我明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期待感还是战胜了所有消极想法。那种期待也是一种希望:如果知道了“문주”的含义,稍微了解了我的起源,我就可以更加光明正大地迎接宇宙了。
那个司机师傅就是在铁路上把我救下的人。
更准确地说,是他紧急刹车,这才救下了差点被火车撞到的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并没有把这个在车前因恐惧而号啕大哭、身份不明的小女孩直接送到警察局或孤儿院,而是带回了他与母亲一起生活的家里,给她起了“문주”这个名字,把她保护起来。如果按曙瑛所说,名字是“家”的话,那么可以说我在“문주”那个家里居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문주”这个名字并无文件记录,也未在政府部门备案,只有司机师傅、他母亲,以及几个邻居这么叫过。而在我进了孤儿院之后,这个名字也就自然消失了。虽然无从知晓我生命的恩人——那个曾一度保护过我的人,为何给我起“문주”这个名字,但我知道这名字显然满怀善意。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唯一在吃饭时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一定要多吃点”的大人。他还经常给我买软饼干;当他母亲催促“赶紧把那个丫头送走”时,他会一把抱起我放到背上,背着我出门,到附近散步。长久以来,我都没有尝试去找他。软饼干的白糖味道、柔软的手掌、硬实的脊骨的触感,还有凝视着我、叫我“문주呀”时在耳边掀起小波动的中低嗓音……仅凭这些琐碎的感觉,是无法找到一个人的。我那时只有三四岁——是保健所医生根据我的成长状态推断出来的年龄,未必准确——还没有聪明到为了未来的重逢,可以提前记下他的名字或那幢韩屋的地址。就连一年前曾邀请我到韩国,对被领养到海外的人士非常友好的民间团体工作人员都没能帮到我。去寻找一个连名字、年龄、身份证号码都不知道的并非家人的人,对他们来说也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找不到他,所以也就无从知道“문주”这个无记录信息的名字的含义了。
门柱。
有一段时间,我曾退而求其次,把希望寄托在“门柱”这样一个事物上。上大学时,有一天,和我做语言交流、互相学习的基贤告诉我,《标准国语大词典》里有“문주”的释义,于是我决定相信词典对“문주”的定义。那天,我盯着基贤的词典,把“문주”词条里的解释读了一遍又一遍——门柱:插在门扇两侧,用于固定门的柱子。其实,那天我很开心。虽然我知道很少有人会把词典里出现的词汇用作名字,但“门柱”对韩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单词,这点我很喜欢。而且,“门柱”给人的陌生感也颇有魅力,这点也让我不胜欢喜。门柱,这个既是支撑屋顶的根基,又是建筑物重量中心的事物,就如同我从未见过的遥远国度里的遗迹一般。
“문주”“门柱”……我反复默念,内心有种得到慰藉的感觉。
然而,不确定的假设无法持续发挥慰藉的作用。我越试图依靠它,我的门柱就摇晃得越厉害,然后一点点地碎掉,渐渐模糊,变得透明。在我领悟到相信某个不确定的信息,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失望后,每当我感到痛苦或混乱时,像念咒语一样反复默念“문주”和“门柱”的习惯也随之消失。慰藉的有效期结束,遗迹也随之封存。
有时朋友们也会问,为什么对以前的临时名字那么执着。对于这个问题,每次我只能给出同样的回答——“문주”是我的起源。在我被叫作“문주”之前,也就是我在铁路上被发现之前的生活,只是黑暗的延长,因此,我完全没有那个时期的记忆。不记得三四岁之前的事情,可能是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大学时期遇到的心理咨询师认为,也可能是因为在铁路上受到了冲击。因为没有记忆,那时的名字——当然亲生母亲也可能把取名这种小辛苦都省略了——已经被埋藏于遗忘的领域。可以说,自我以“문주”的身份开始生活的那一刻起,我才算拥有了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成为一个完整的存在,了解了甜味与苦味,遇到喜欢的东西知道说喜欢,感受到无聊、委屈和抱歉的情感。所有有关“第一次”的记忆——第一次开口讲的话,第一次去餐厅和理发店的情景,第一次笑和第一次哭的原因,第一次明白“被抛弃”的含义的那一瞬间,这些都属于我是“문주”的那些日子。只有了解了“문주”的含义,我的历史才能被开启。
在一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