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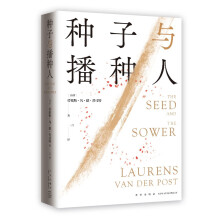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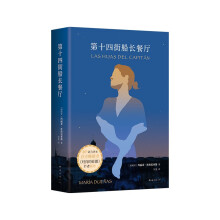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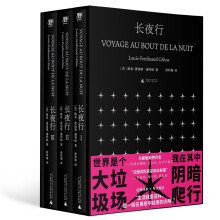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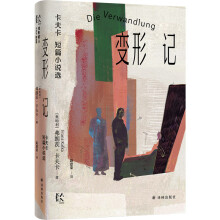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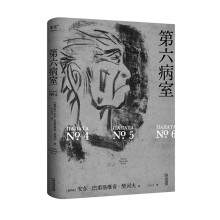
●移民之国的一场人性试炼 战争、贫困、动乱、流感……在这失控的岁月里,我只想竭尽全力地活下去!
●美国版《活着》 真实描摹德裔美国人不堪回首的“敌国侨民”岁月 当我的名字成为我与生俱来的罪过,当身份成为偏见与仇恨的理由,我们只能用自己的体温一点点融化坚冰。
●取材自作者真实的家族经历 作者的母亲就是书中在1918年流感肆虐时降生的那个小女孩。作者用诗意的语言,让百年前的历史在字里行间鲜活重现。
窗外,平原一望无垠,没有色彩,也没有变化。清晨看起来像是正午,整个白昼也可以如同夜晚一般。地平线,即天空与地面相接的那条线,消失了;远处与近处毫无区别。透过结了霜的车窗向外看去,若有任何形状出现,那形状也只有大小之分。大多数时候,你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
在这样的日子里,世界萎缩到每个人都能一目了然的程度。天地合一之际,唯有自我可作为参照。除开火车停站之时,车上的大多数乘客都陷入了一种沉默的恍惚之中。一月的风掠过没有树木的平原,刮起一阵刺骨的寒雪打在车窗上,发出嘎嘎的声响;迎风而行的列车也会时不时地打起哆嗦来。人们为了保暖,穿着大衣,盖着毛毯,抑或裹着牛皮做的睡袍,挤作一团。行驶中的火车有种催眠奇效,让格尔达从前一晚读到电报就开始狂跳不止的心脏镇定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心里踏实了一些,便让孩子们一直玩着手指游戏,或者让他们猜谜语,后来,有节奏地行进着的火车哄着孩子们入了眠。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世界打她身边经过。
过道对面坐着另一个女人,除格尔达外,她是唯一在斯图尔特站上车的女士。启程之际,手忙脚乱的格尔达几乎没注意到她,而现在,她跟大多数其他乘客一样,也打起了瞌睡。在一片寂静中,格尔达打量起那女人的衣服来,发现衣服的剪裁很复杂,看起来是裁缝,而不是农妇缝制的。她注意到了诸如袖口是机器缝的,而非手工缝制再熨烫平整等细节。她看了看自己的袖子上的褶皱处,跟那女人的衣服做了做比较。那女人带着的旅行包是酒红色的,颜色很深,用的布料很厚实,包面上绣着图案,还配有皮质手柄和黄铜配件。初看时,格尔达并未注意到旅行包的边角有一处磨损,也未注意到接缝处有一处缝补得很糟糕的破洞,可一旦注意到这一切,她随即也注意到这件剪裁讲究的衣服的下摆有些破损,而且那女人的外套肘部都磨得发亮了。她更加仔细地打量起那女人来。那女人看上去疲惫不堪;尽管她的脸在睡梦中已经松弛下来,但她看起来仿佛非常需要休息。连裹在腿上的毯子滑落到地板上,她都没有反应。格尔达把手伸过去,拾起毯子,塞到了那女人的背后与座位之间。
只有那些离车厢前排的火炉最近的人似乎还能四处走动或与人闲聊。位于车厢中部的格尔达看着坐在前排长椅上的三个男人。他们也是那天早上在斯图尔特上的车,他们三个急匆匆地冲在两位女士前面,更像是不守规矩的男孩,而不是成年男子。此时,他们时而发出吵闹的喊声,时而相互发出嘘声,示意对方安静下来,他们专心玩着某种游戏,像是在掷骰子,又像是在玩纸牌;不过她看不清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他们尽管很孩子气,却是一副工人的模样。他们的面色都很红润,这是在平原上典型的极寒和酷暑的极端环境下劳作过的缘故。他们朴素寻常的衣着,使她想起了她最开始给弗里茨做的、后来又经常给他缝缝补补的那些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