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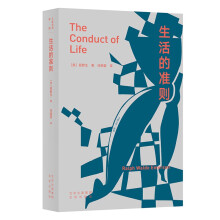









一
黄昏时分,赫尔格•格拉姆从街角拐入孔多蒂大街。 一支军乐队正昂首阔步地行进在街面上。此刻,乐队正在演奏着一曲《风流寡妇》,那急速疯狂的旋律听上去仿佛是一阵粗粝的号角声。冬日的下午,这群身材矮小、肤色黧黑的士兵从他身旁匆匆走过,那架势给人感觉不像是和平时期准备返回营房吃晚饭的队伍,倒像是一队古罗马军团正准备冲进蛮敌阵营与其来一场殊死厮杀。也许正因如此,他们才显得这般匆忙。一想到这,赫尔格不禁微微一笑。他站在街角目送着远去的乐队,将大衣领子竖起以便抵御寒风,感觉浑身被一种独特的历史氛围所裹挟。随后他信步朝科尔索大街的方向走去,下意识地听见自己正在哼着刚才那支曲子。
走到街角处他停下来四下张望,哦,那么这儿就是科尔索大街了——川流不息的马车行驶在拥挤的街面上,狭窄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摩肩接踵的人群。
他停在原地,驻足不前。看着如潮水般涌过身旁的人群和车辆,不禁冒出一个令他自己都觉得可笑的想法:他可以每天晚上黄昏的时候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这条街上漫步,直到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如同对他的家乡克里斯蒂安尼亚一样熟悉。他突然有一股冲动,想从这里一直走下去,也许就这样走上整个晚上,把罗马所有的大街小巷都走个遍。他在脑海中想象着这座城市的模样,罗马应该就是刚才落日时分从宾乔公园山上俯瞰到的样子。
西边的天空布满了云层,堆积在一起如同浅灰色的羔羊毛。西沉的落日将云层涂抹成辉煌的琥珀色,城市慵懒地躺在灰色的天空下。赫尔格知道这才是现实中的罗马,与他想象中的梦幻罗马不一样,这是真实的罗马。
这趟旅行沿途所见令他颇为失望。一切都与当初在家中所渴望的那种出门见世面的愿望大相径庭。不过最终有一座城市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那就是罗马。
脚下的山谷里有一大片屋顶,各种样式的新旧房屋高低错落。这些建造于不同年代的房子给人感觉仿佛是在一种很随意的状态下临时搭建起来的,只为应付眼前一时之需。屋顶之间偶尔露出的几块空地就是街道。所有这些不经意的线条,彼此交集,构成错综复杂成百上千的角度,静静地、懒洋洋地横陈在黯淡的天空之下。落日给云层的边界点缀上一抹亮色,空气中飘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如梦似幻。没有工厂烟囱的痕迹,从下面房屋顶端伸出来一 个个小小的烟囱,看不见有烟雾从屋顶排出来,也没有任何烟柱升到空中去破坏这层薄雾。圆形的铁锈色旧屋顶上,长满了褐色的苔藓和杂草,屋檐的泄水槽里开着无名小黄花。观景平台的边缘种了一长溜龙舌兰,直挺挺地立在花盆里。枯萎的藤蔓从屋角垂落。那些建在高处的房屋,比它们的邻居高出一大截,露出黑魆魆的窗洞,要么正对着对面房屋灰黄色的墙壁,要么在闭合的百叶窗后昏睡。远处的凉廊,好似古时的瞭望塔,连同那些铺着瓦楞铁皮屋顶的避暑小木屋,一同在薄雾中隐约可见。
飘浮在所有这些之上的是教堂的圆顶。其中有一个特别巨大的灰色圆顶,在赫尔格看来,它应该是位于远处河流对岸的圣彼得大教堂。
山谷远方,鳞次栉比的屋顶下躺卧着静静的城市。今夜的情景恰与它“永恒之都”的绰号相得益彰——远处有一座低矮的山峰,山脊绵延迤逦,伸向地平线的远方。沿着山脊长满了密密匝匝的松林,颀长的树干托着浓密的树冠。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后方,可以看到另一座山,山上的别墅点缀在松柏之间。那大约是马里奥山。
冬青树暗绿色的叶子在他的头上撑起一顶华盖,水从他身后的喷泉喷涌而出,泉水飞溅到石头台阶上,发出生动的泼水声,再缓缓流入下面的池子里。
赫尔格对着他梦中的城市喃喃自语——虽然这里有他尚未涉足的街道,房子里住着他完全不认识的人:“罗马,罗马,永恒的罗马。”他被一阵突袭而至的孤独感捕获,惊异于自己的伤感,虽然明知此刻不会有人注意,他还是急遽地转过身子,匆匆走下西班牙台阶。
此刻,站在孔多蒂大街与科尔索大街的交汇处,赫尔格感到一阵眩晕,同时还有一种夹杂着喜悦的焦虑。他只想融入眼前的车水马龙之中,去探索这座陌生的城市,一直走到圣彼得广场。
过马路的时候,迎面走来两个年轻姑娘。她们看上去像挪威女孩,他自忖道。心里一阵欢喜,其中一个姑娘肤色白皙,穿着一件浅色皮衣。
哪怕只是读读马路边上那些由拉丁文刻写在房角白色大理石上的街牌,他都感觉快乐无比。
他走到桥边的一块空地,桥上的两排路灯在黯淡的天光下发出绿幽幽的光。河流两岸有一长溜低矮的石头栏杆,沿着栏杆种了成排的树木,枝叶枯萎,大块的白色树皮剥落在地上。河对岸的街灯在树丛中闪烁,房屋在天光的衬托下显得黑乎乎的,影影绰绰;但是在河的这边,从玻璃窗上仍可看到夕阳反射出来的光芒。此刻,云层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小山的松树林之上,天空呈现出透明的蛋青色,偶尔可以看见几丝惊艳的殷红色的游云,在天边缓缓移动。
他站在桥上低头看着下面的台伯河。河水波澜不惊,快速地流淌着。河面倒映着傍晚天光的颜色。河水夹带着枯枝败叶和泥沙,在两岸的石坝之间一路冲将而去。桥边有一小段楼梯可以直达河边。原来这么容易就可以走下去,如果哪天有谁不想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想过,他寻思着。
他用德语向一个警察问路,去圣彼得大教堂怎么走。那人先用法语回答他,然后再说一遍意大利语,看到赫尔格在反复摇头,他又说一遍法语,用手指着河流上方,于是他转而朝那个方向走去。
眼前矗立着一幢黑色的巨石建筑,直插云天,这是一座有着锯齿状矮墙脊的环形高塔,在塔的顶端有一个乌黑的天使剪影,凭着这轮廓他辨出这里是圣天使城堡,于是径直往前走去。天色还未完全黑透,桥头的几尊雕像在暮色中隐约泛出橘色的光泽,绯红的天光映照在流淌的台伯河水面。圣天使桥远处,一辆电车正驶过一座新建的铁桥, 车窗内灯火通明,电车缆线时不时地划擦出白色的电光。
赫尔格摘下礼帽向一个人问路:
“圣彼得大教堂?”
那人用手指了一下,说了几句他听不懂的话。赫尔格拐进一条狭窄昏暗的街道,心里有一种欣喜的感觉,他觉得这条路似曾相识,因为这与他想象中的意大利街道如出一辙。一家又一家的古玩店,他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些光线黯淡的橱窗,大多数东西都是赝品——那些挂在绳子上的脏兮兮且做工粗糙的白色花边显然都不是真正的意大利手工货。灰扑扑的盒盖里摆放着一些陶器碎片、泛着铜锈绿的小雕像、新旧铜制烛台、胸针,还有成堆的石头,一看 就不是什么真货。但是他心里还是被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所占据,他想走进去买点什么——去询价,讨价还价,然后再买下来。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他已经一脚跨进了一家小店。店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天花板上挂着教堂的吊灯,红绿白各色的绸布,上面用金线绣着花朵,另外还有几件破家具。
柜台后面有个年轻人正在看书。他肤色黝黑,下巴微微发青,没有刮胡子。赫尔格指着店里的东西问:“多少钱?”他只听得懂价钱,这些东西还真够贵的。他实在是不应该买什么,尤其当他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也无法讨价还价的时候。
架子上摆着几只洛可可风格的瓷像和饰有玫瑰花枝的花瓶,看上去挺有现代感。赫尔格随手抓起一件拿到柜台上,问道:“多少钱?”
“7里拉。”年轻人伸出7根手指头。
“4里拉。”赫尔格从他咖啡色皮质新手套里伸出4根指头,他对自己在外语学习上的飞跃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那人说的一大通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只是每当他停下来,他就伸出4根指头,重复报价,再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补上一句:“这不是古董哦!”
店主表示抗议:“是真的古董。”“就出4里拉。”赫尔格再次重复——那人现在举起的手指只剩下5根了——赫尔格开始朝门口走去。那人把他叫回来,让步了。赫尔格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最后他拿起那件裹着粉色包装纸的东西走出了店门。
远处,在街道的尽头,天空下那团黑乎乎的建筑应该就是教堂了,他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他匆匆穿过广场的前端,两旁是明亮的橱窗,有轨电车朝着两个半圆形的、如同一双张开手臂的环形拱廊驶过去,好似要直接开进那黑暗幽静的教堂里面。蚌壳状的宽大台阶朝着广场的方向延伸出来。
教堂的圆顶以及沿着拱廊的屋顶矗立着成排圣者雕像,在微明的天光衬托之下呈现出黑色的剪影。教堂后面的树木和房屋如同一些不规则的时尚作品,彼此摞叠。街灯昏暗,黑暗弥漫在巨大的圆柱之间,顺着开放式柱廊沿着台阶漫延而下。他缓慢地拾级而上,走近教堂,隔着铁门向内张望,然后再走回广场中央的方尖碑,凝视着眼前这座黑乎乎的巨型建筑。他仰起头,目光由下至上顺着这根修长笔直的石针移动,方尖碑的顶端直插夜空,最后几片薄 云悬挂半空,在渐浓的夜色中,星光初现。
他又听见有水流入石槽的声音,水从一处流往另一处,柔声轻拍,水波荡漾。他走近其中一个喷泉,只见粗壮的白色水柱喷涌而出,肆无忌惮地朝着天空喷射,在透明的空气中形成一柱黑色的喷泉,然后重新跌入水池之中,在黑暗里隐约泛出银白的水光。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喷泉,看呆了。直到一阵劲风吹过,将空中的水柱改变方向,冰冷的水珠喷了他一脸。他依然待在原地不动,全神贯注,侧耳倾听。他往前走几步,停下来,再慢慢地向前走几步, 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这么说,他真的是在这儿了,远离所有他曾渴望逃离的一切,蹑手蹑脚地,如同囚犯逃离监狱。
街角有家餐厅。他朝它走过去。途中路过一家香烟店,他停下来买了几包香烟、几张明信片和几枚邮票。等牛排的时候,他一边大口喝着红酒,一边给父母写信。他对父亲写道:“今天我时不时地就会想到您。”真的是这样。然后写给母亲:“我今天给您买了一件小礼物,这是我到罗马之后买的第一件东西。”可怜的母亲,她还好吗?最近这些年,他动不动就对她表示出不耐烦。他打开包装纸,仔细察看这个小玩意儿,它应该是个香水瓶子。他又在信里添了几句话,告诉她,他在这边意大利语还能对付得过去,甚至在商店里与人讨价还价都不在话下。
晚餐很好,就是贵点。不过没关系,一旦他对这边的情况熟悉下来,自然会有办法让自己过得经济实惠的。红酒令他兴奋而满足,走出餐厅他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经过一长排低矮破旧的房子,穿过拱门他来到一座桥上。 栅栏那边有人拦住他,让他付一个钢镚儿的门票钱。桥的另一端是一座带圆顶的大教堂。
他走进一片迷宫般又黑又窄的街道——在神秘莫测的黑暗中,根据眼前突起的飞檐和格子窗户他大约能猜出这里是些废弃衰败的宫殿,它们和许多破旧的茅屋密密地挤在一起。小教堂前面的庭院被成片的房子夹在当中。没有路可走,一不小心他的脚踩在排水沟腐烂的垃圾上。亮着灯的小酒馆窄门外,几盏街灯下依稀可辨几个人影。
他半惊半喜,如孩子般激动。有点担心自己待会儿怎样才能走出这迷宫般的街道,如何才能找到回酒店的路。也许得叫辆出租车了,他揣度着。
他走过另一条几乎空无一人的小巷。头顶上方,高耸的房屋之间露出一截晴朗的蓝天。这些房子的窗户都没有窗框,看上去好像在墙上直接挖出一个个的黑洞。一阵轻风吹来,那些散落在石桥上的杂草、纸屑和尘土,在凹凸不平的桥面上随风起舞。
两个女子走在他身后,在一盏路灯下经过他身旁。他愣了一下,即刻认出她们就是今天下午在科尔索大街上他注意到的两位姑娘。他觉得她们是挪威人。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位高个子穿浅色皮衣的女子。
突然,他心里生出一种冒险的冲动,他想向她们问路,以此判断这两位姑娘是不是挪威人,或者至少是不是北欧人,她们看上去显然像是外国人。按捺住一颗跳动不安的心,他开始尾随她们。
两位姑娘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商店已经打烊了。于是她们继续往前走。赫尔格在心里琢磨着他应该用哪国语言来与她们打招呼,是说“请问”还是“Bitte”或者“Scusi”——抑或就直接用挪威语发问,如果她们真的是挪威人,那就太有意思了。
两位姑娘在街角拐过一个弯,赫尔格紧跟几步,鼓足勇气走上前和她们搭讪。矮个子姑娘怒气冲冲地回过头来,用意大利语嘟囔了几句。他好生失望,打算向她们道歉一声就溜之大吉。就在这时,他听见那位高个子姑娘用挪威语说道:“你不该搭理这种人,塞斯卡。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没听见他说话。”
“我实在是气不过这些该死的意大利流氓,他们从来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女人。”另外那位姑娘说道。
“对不起。”赫尔格说道,两位姑娘停下来,飞快地转过身。
“请你们原谅我。”他嘟囔着,脸色涨红,而且当他意识到这点,脸红得更加厉害了。“我今天刚从佛罗伦萨到这儿,在这曲里拐弯的地方迷路了。我猜想你们是挪威人,或者至少是北欧人。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能不能麻烦你们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出租车?我叫格拉姆。”说罢,他把头上的帽子抬一抬。
“你住在哪里?”高个子问道。
“我住在一个叫阿尔伯格•托日诺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近。”他解释道。
“他得走到圣卡罗站去搭乘特拉斯泰韦雷电车。”另外那位姑娘说道。
“不,最好是到新科尔索大街坐1路电车。”
“那些车都不到终点站。”小个子姑娘说道。
“不是的,它们到的。站牌上写有圣皮埃托站和火车站。”她转身对赫尔格解释道。
“哦,那趟车啊!它要经过卡珀勒卡斯和路德维西,绕得可远了,搭那趟车至少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火车站。”
“不是的,亲爱的,它走直线——直接沿着主干道走。”
“不对,”另外那位姑娘坚持道,“它先朝拉特兰站的方向开。”
高个子姑娘转向赫尔格:“你在前面右拐走到一个市场。从那里你沿着左边的坎色拉里大街一直走到新科尔索大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电车站就在坎色拉里大街——反正离那里不远的地方——你会看到站牌的。但是你要记得选乘标有圣皮埃托站和火车站方向的1路车。”
赫尔格站在那里,觉得有些丧气。听着两位姑娘滚瓜烂熟地说着一长串外国地名,摇头道:“恐怕我一辈子也找不到那里,我还是走走看能不能拦一辆出租车吧。”
“也许我们可以陪你走一小段路到车站。”高个子说道。
小个子姑娘用意大利语在一旁低声抱怨几句,但是显然她的同伴态度坚决。赫尔格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这一切只是让他更加觉得云里雾里。
“谢谢你们,不用麻烦了,我相信我会找到回酒店的路的。”
“不麻烦,我们顺路。”高个子姑娘一边走一边说。
“那真是太感谢了。我发现在罗马认路还真是件挺困难的事儿,你们觉得呢?”他没话找话,“尤其是天黑的时候。”
“没那么难,你很快就会摸清方向的。”
“我是今天才到的。今早从佛罗伦萨搭火车来的。”小个子在一旁用意大利语小声低语。高个子姑娘问道:“佛罗伦萨那边冷吗?”
“非常冷。这边气候显得要暖和一点,是不是?总之昨天我给我母亲写信,让她给我把冬衣寄过来。”
“这边有时候也挺冷的。你喜欢佛罗伦萨吗?你在那边待了多久?”
“半个多月吧。我觉得我会更喜欢罗马。”
旁边那位姑娘笑了笑——她一直在用意大利语嘟嘟囔囔——但是那位高个子姑娘继续用她愉悦平静的声音与赫尔格交谈:
“我也觉得再没有哪座城市能比罗马更让人动心的了。”
“你朋友是意大利人?”赫尔格问道。
“不是。雅赫曼小姐是挪威人。我们在一起说意大利语是因为我想学习,她的意大利语非常好。我叫温格。”她补充道,“到了,前边就是坎色拉里。”她指着前方一座黑乎乎的大宫殿。
“它的庭院真的像报道上说的那样好吗?”
“是的,非常漂亮。我来告诉你该乘哪趟车。”他们正在等车的时候,从对面街上走过来两个男人。
“嘿!你们在这儿呀!”其中一个人喊道。
“晚上好,”另外一个人和她们打招呼,“多巧啊!咱们可以一起走,你们后来买到珊瑚了吗?”
“那家店关门了。”雅赫曼小姐闷闷不乐地答道。
“我们刚才碰到一位老乡,答应给他带路到电车站。”
温格小姐一边解释,一边为他们做介绍,“格拉姆先生——这位是艺术家赫根先生;这位是艾林,雕塑家。”
“您还记得我吗?赫根先生,我是格拉姆,三年前咱们在迈索塞斯特见过。”
“哦哦对的,当然记得。这么说您来罗马了?”
艾林和雅赫曼小姐两人站在一旁窃窃私语。然后她走到她朋友身边说:“珍妮,我想回家了。今晚没兴趣和你们到法斯卡迪了。”
“可是亲爱的,是你提议说去的呀。”
“好吧,反正无论如何我不想去法斯卡迪——我的天!坐在那种地方和30多个分不清年龄和性别的丹麦女人挤在一起,想想就可怕。”
“那就去别的地方呗。哦,格拉姆先生,你的车来了。”
“万分感谢。咱们还会再见面吗?也许,在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
电车停在他们面前。温格小姐说道:“不知道呢——也许您愿意加入我们,我们几个正打算找个地方喝一杯,听听音乐。”
“谢谢。”赫尔格犹豫了一下,有点尴尬地看了看旁边几位,“我当然很乐意了。不过——”他转身自信地看着和颜悦色的温格小姐,局促地笑道:“你们彼此都是熟人,也许不想让一个陌生人掺和进来?”
“没有的事儿。”她微笑着,“这样最好了。瞧,你的车也走了。再说你和赫根先生之前就认识,现在又认识了我们。待会儿我们把你送回去。如果不觉得累的话,咱们就走吧。”
“累?一点儿也不。很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赫尔格热切地回答道。
其他几个人开始推荐不同的咖啡馆,赫尔格一个字也听不懂;他父亲从来没和他提起过这里的咖啡馆。雅赫曼把大家的提议全部给否掉了。
“好吧,那我们就去圣•奥古斯提诺。贡纳,你去过那家的,他们提供一流的红酒。”珍妮迈步往前走,赫根走在她身旁。
“那里没有音乐。”雅赫曼小姐反驳道。
“当然有啦,那儿有个斜眼的家伙,还有其他几个乐师,他们几乎每晚都上场。走吧,别浪费时间了。”
赫尔格紧跟在雅赫曼小姐和那位瑞典雕塑家的后面。
“你来罗马多久了,格拉姆先生?”
“不久,今天早上才从佛罗伦萨过来的。”
雅赫曼爆发出一阵大笑。赫尔格感觉自己备受冷落,也许刚才他就该推托自己累了,独自离开。他们走在漆黑狭窄的街道上,雅赫曼小姐一路都在与那位雕塑家聊天,他几次想和她搭讪,她都爱搭不理。正当他下定决心想要离开的时候,他发现这两人在他前面街边的一扇窄门处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