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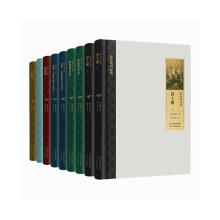






• 伊迪丝•华顿是二十世纪美国深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快乐之家》、《纯真时代》等在我国读者中很有影响。《伊坦•弗洛美》是其重要作品。
•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译本。本书译文是吕叔湘在四十年代翻译的,但是后来做了一次修订,保证了现代汉语的习惯。
• 《伊坦•弗洛美》从主人翁伊坦•弗洛美人生的四个时期:少年时期,结婚时期,外遇时期,老年时期来分析他的悲剧人生,并指出华顿创作此悲剧的原因,从而使读者更好地把握华顿作品中 的悲观意蕴。
整个的乡镇埋在两尺深的雪的底下,迎风的墙角有更深的雪堆。在铁色的天空,北斗的星点像冰柱,南天的猎户星射出寒冷的光芒。月亮已经下去,但是夜色清朗,榆树中间的一所所白色的房子让积雪衬托着变成灰色,灌木丛在那上面造成一些黑的斑点。教堂的地下室的窗户送出一条条黄的灯光,远远地横在无穷的雪浪之上。
年轻的伊坦•弗洛美顺着已经没有行人的街道快步走去,走过银行和迈克尔•伊迪的新杂货铺,走过门前有两棵挪威枞的华努谟律师的住宅。正对着华家的园门,马路开始下降往考白里谷地去的地方,矗立着教堂的黄条的白色的尖顶和细瘦的列柱。教堂的上层窗户是黑的,但是从下层的窗户里,沿着那地势陡然下降到考白里路去的一边,长长的光线射了出来,照出那通到地下室门口去的小路上面的一些新的脚印,并且照见近旁的木棚底下一溜雪车和重重地盖着毡毯的马匹。
夜很静。空气干燥而洁净,叫人不很觉得冷。在弗洛美的感觉,仿佛是完全没有大气,仿佛是在他脚底下的白色的大地和他头顶上的金属般的穹粱之间没有比以太更浓的东西横亘在中间似的。“倒像是在蒸汽已经跑完了的蒸馏器里头,”他肚子里想。四五年之前,他曾经在乌司特的工业学校里读过一年的课程,跟一位蔼然可亲的物理学教授在实验室里掇弄过一程子;虽然他回家以后过的是另一种生活,在那儿得来的许多印象还常常复现,在想不到的时刻,经由迥不相同的别种联想。他的父亲的死和相继而来的种种不幸使弗洛美不能继续求学;但是他所学的课程虽然很浅薄,不够有什么实用,却已经滋长了他的想象力,使他隐约感觉在一切事物的日常面目之后隐伏着巨大而模糊的意义。
当他在雪地里迈步前进的时候,这个意义之感觉在他脑子里炽盛起来,和他身上因疾行而生的体热混合在一起。走到街尽头,在教堂的黑暗的正面之前,他收住了脚步。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急剧地呼吸着,朝街的这头和那头看望,一个人影子也没有。从华律师家门口那两棵枞树往下去那段考白里大路是斯塔克菲尔镇上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滑雪场,在星月之夜,教堂的转角处滑雪的人笑语喧哗,往往到半夜;但是今天晚上在那雪白的斜坡上看不见一个雪橇的黑点子。午夜的肃静罩住这个乡镇,镇上还没有睡觉的人全都聚集在这教堂的窗户的背后,从那里边跳舞的音乐随着灯光流到外边来。
那个年轻人绕着教堂的侧边往地下室的门口走去。为了避开里面射出来的明朗的灯光,他在未经践踏的雪地里绕个圈儿走过去。一直藏在黑地里,他一步一步地挨近第一个窗户,把他的瘦长的身子靠后,把他的颈项伸长,偷偷地窥视屋子里边的情形。
从他立足的洁净寒冷的黑地里看过去,这个屋子好像在热雾当中沸腾。煤气灯的金属射光板把一阵阵的光波射到白粉墙上,屋子那头的煤炉门像是吐送火山里出来的火焰。屋子当中挤满了年轻的男和女。顺着朝对窗户的墙壁摆着一排椅子,坐在那儿的岁数较大的女人们刚刚站起。这个时候音乐已经停止,乐师们——一个拉提琴的和一个星期日弹小风琴的青年女子——正在餐桌的一角匆匆进食,那张桌子放在屋子一头的讲台上,一桌子的吃空了的烤面饼盘子和冰淇淋碟子。客人们已经准备散会,人们的脚步已经趋向悬挂衣帽的过道,忽然一个两脚矫捷一头黑发的青年男子跳到屋子的中央,拍动他的手掌。这个记号立刻发生效力。乐师们疾疾走到他们的乐器跟前,跳舞的人——有几个已经穿上外衣——在屋子的两边排列成行,年长的旁观者又在椅子上坐下;那个青年在人堆里钻来钻去,终于拉出一个业已在头上蒙上一条樱桃色披巾的女子,引她走到舞场的尽头,然后合着一支维吉尼亚旋旋舞的轻快的曲子旋风似的领着她向场子的这一头舞了过来。
弗洛美的心跳得快起来。他正在伸长了脖子寻找那块樱桃色披巾底下的人面,没想到另外一双眼睛比他的眼睛更快。那个旋旋舞的领步人——他的容貌透着有爱尔兰人的血统——舞得很高明,他的舞伴感染了他的热情。她一路舞了过来,她的轻盈的身子从这边摇到那边,圆圈儿越转越快,披巾飞了起来,飘扬在肩膀背后;她每一转身,弗洛美瞥见一下她的笑着喘着的双唇,她的覆额的乌云似的黑发,和她那一双黝黑的眼珠,这好像是这一团翻飞不定的线条之中唯一固定的两点。
跳舞的一对越舞越快,乐师们为了凑合他们的步子,使劲打击他们的乐器,像赛马的人在最后一截路上拼命抽打他们的坐骑一般;可是在窗子外边的那个年轻人看来,这场旋旋舞像是永远没有尽期。他时而转移他的目光从女子的脸上到她的舞伴的脸上,那个脸在跳舞的狂热之中俨然有“佳人属我”的神情。邓尼斯•伊迪是迈克尔•伊迪的儿子,迈克尔•伊迪是那个野心的爱尔兰杂货商,他的花言巧语和厚脸皮使斯塔克菲尔镇上的人初次尝着“新式”商业方法的滋味,他的新盖的砖墙铺面是他的成功的明证。他的儿子大概要继承他的事业,而同时在应用同样的技术征服着斯塔克菲尔的青年女子。在今日以前,伊坦•弗洛美只是肚子里说他是个卑鄙的家伙,可是现在恨不得拉他出来痛痛快快给他一顿鞭子。奇怪得很,这位姑娘好像一点也不觉得他这个人的讨人嫌:她居然能和他笑脸对笑脸,她居然能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
弗洛美惯常步行到斯塔克菲尔街上接他女人的表妹玛提•息尔味回家,在镇上的节令宴聚把她吸引了来的那些个不常有的晚夕。玛提初来他们家里住的时候,是他的女人说的,这种娱乐的机会不要让她错过。玛提是斯丹福城里人,当她加入弗洛美的家庭作为细娜表姐的帮手的时候,他们觉得,她既不拿工钱,最好不要让她太感觉沉闷,斯塔克菲尔农家的生活和她过惯了的城市生活太悬殊了。倘若不是因为这个——弗洛美半嘲半恨地想——细娜是再也不会留心到这个女孩子的娱乐问题的。
他的女人初次提议放玛提晚出一次的时候,伊坦心里老大的不愿意,在田里辛苦了一天之后还要他额外跋涉两英里到街上,再两英里回来;但是不久之后他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巴不得斯塔克菲尔夜夜都有聚会。
……
自序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