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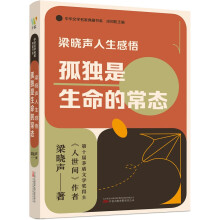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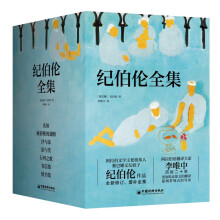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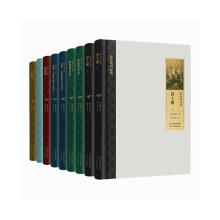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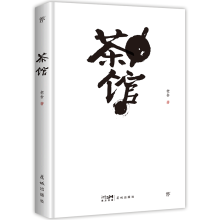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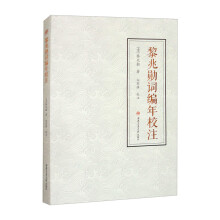
“英国小说家中最伟大的悲剧作家”“英国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哈代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关于某时某地生活的写照。这是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展现在一种强烈的想象力、一种深刻的诗意的天才和一颗温柔而仁慈的心灵面前时所显示出来的幻象”。
他使劲琢磨,在这一片微光里,学校的老师到底在哪一个点儿上哪——现在老师跟村子里的人一直没有来往了;在这儿,老师对于村人好像已经死了。但是他却好像看见了费劳孙在那片白光里安闲地散步,像尼布甲尼撒王窑里的人①一样。
他曾听人说过,微风的速度一个钟头是十英里,他现在想起这个事实来了。他冲着东北,张开了嘴,好像喝甜的液体似的,把风吸到肚子里。
“你呀,”他带着轻怜痛惜的口气对着风说,“在一两个钟头以前,还没离开基督寺哪,那时候你还悠悠地在它的街道上飘动,团团地把它的风信旗吹转,轻轻地在费劳孙先生脸上掠过,深深地让他把你呼吸哪,这会儿哪,你可来到了这儿,让我呼吸了——那时的你也就是现在的你啊!”
忽然风里朝着他传来了一种东西——好像是由那个城市传来了一种使命——还好像是由一个住在那儿的人发来的。一点不错,那是钟的声音,那正是那个城市的声音,轻缈而悦耳地对他呼唤,说:“我们这儿快乐!”
在他这样神飞魂荡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地了,他使劲集中注意力,才恢复了知觉。在他站立的那座山头下面几码远的地方,出现了几匹马,拉着一辆车走来,那本是由那个陡峻的山坡底下,蜿蜒地走了半个钟头的工夫,才走到那儿的。它们拉的是一车煤——想把那种燃料弄到这块高原上来,只有走那条路才成。跟在车旁的是一个车夫、一个助手和一个小孩,那小孩正用脚把一块大石头,弄到车轮子的后面,把车顶住了,好让那几匹喘息不定的畜生,好好休息一下。另外那两个人,就从车上的煤堆里,拿出一大瓶酒,开始轮流着喝起来。
他们两个都是快上年纪的人,说起话来和声柔气的。裘德跟他们打招呼,问他们是不是从基督寺来的。
“拉这么些重东西,从基督寺来?”他们说。
“我的意思是指着那面那个地方说的。”他对基督寺简直都爱得情痴意醉了,因此,他像一个年轻的情人对他爱的女人那样,第二次要提那个地方的名字,都害起羞来。他把天上那片亮光指给他们看——要是让他们自己看,那他们两个那种老眼,是不大能辨得出来的。
“不错。东北面是有一块地方,比起别的地方来,多少亮一点点儿,不过让我自己看,我是看不出来的;没有疑问,那就是基督寺。”
原先裘德腋下夹着一小本故事书,预备趁着天还没黑的时候,在路上读,现在那本书,从他的腋下溜下来了,掉在路上。他把书拾起来,把它理直了,那时候,那个赶车的就在一旁瞅着他。
“啊,小伙子,”他说,“你要是想念他们那儿的人念的那些书,那你的脑袋瓜儿可得改改装——可得倒一个儿才成。”
“为什么?”那孩子问。
“哦,像我们这种人能懂得的东西,他们是从来连正眼都不瞧的,”那个赶车的想借谈话消磨时光,所以接着说,“他们那儿,只说外国话,还都是洪水以前、没有两家人说话一样的时候说的那些外国话①。他们念起那一类东西来,跟夜莺扑打翅膀一样地快。那儿讲的净是学问——除了学问没有别的。自然还有宗教,不过即便宗教也是学问,因为我多会儿也没能懂过那个。不错,那真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地方。话虽如此,那儿到了晚上,街上也一样有不正经的女人乱窜。他们在那儿栽培牧师,就像在地里栽种萝卜一样,我想这你总知道吧?虽然要——多少年的工夫,巴伯?——啊,五年的工夫,才能把一个游手好闲、笨手笨脚的小伙子,栽培成一个老成千练、没有毛病的讲道师,但是只要办得到,他们还是要栽培——还是要把一个人训练得很文雅,把他们训练得老板着面孔,穿着黑色的褂子和背心,戴着讲道师的领子和帽子,和《*经》里那些人的穿戴打扮一样,闹得有时连他自己的妈都不认得他啦。……不是每个人都得有个事儿做才对吗?这就是他们那儿的事儿。”
“你怎么知道——”
“小伙子,别打岔。长辈儿说话的时候,永远不要打岔。把那匹马往旁边拉一拉,巴伯!有人来啦。……你要明白,我这儿是谈大学的生活哪,他们过的都是高尚文雅的生活,这个绝不含糊,尽管我个人并不很看得起他们。
……
第一部 在玛丽格伦
第二部 在基督寺
第三部 在梅勒寨
第四部 在沙氏屯
第五部 在奥尔布里坎和别的地方
第六部 重回基督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