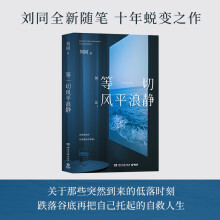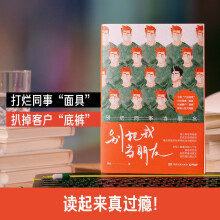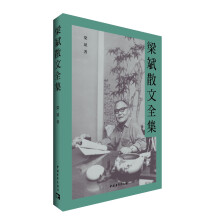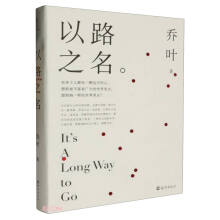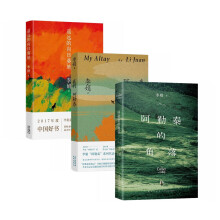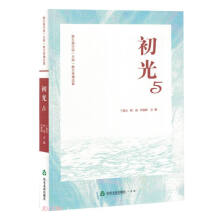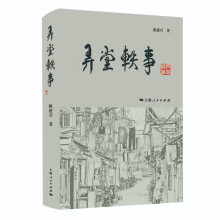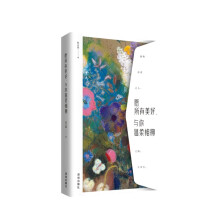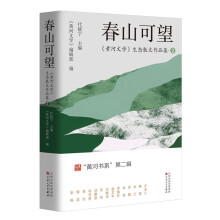甜物质
“这一生,你可能偶尔经过甘蔗田/偶尔经过穷人的清晨/日子是苦的,甘蔗是甜的”“曾经,甘蔗林沙沙响,一个穷人/也有他的神:他把苦含在嘴里,一开口/词语总是甜的”。
1
一个女孩儿在“知乎”上分享她的恋爱经历,提到一个很小很温暖的细节:男孩儿在加她微信时,悄悄往她手心里塞了一颗糖。因为这颗糖,这个普通的爱情故事忽然焕发出幽静、甜美的气息,好似一个孤单的旅人忽然被置于时光的绵长与温情之中。人类对甜味的迷恋几乎是永恒的。一个小孩儿总无法抵挡糖果和故事的诱惑,而成年人,对甜的渴望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对甜味的追求早已超出人类的味觉范畴,成为镌刻在遗传基因里的神秘物质,代代相传。不仅人类,动物也嗜甜,蜂蜜是蜜蜂精心酿造的甜物质,蜂鸟每天摄人的糖要占体重的一半,而蜗牛最喜欢吃草莓、香蕉、橘子等甜果。另外,蔬菜瓜果上的寄生虫也是甜的忠实粉丝。经济不好时,糖果的销量却很好。糖不仅是食物,它的甜,还给人带来安慰。艰难岁月里,糖果营造了味蕾上的天堂。一颗紧攥在手心舍不得舔舐的糖果,成了延迟享受的美味及一生幸福的隐喻。
人类社会,随着时间流逝,甜味越来越浓。就像茶叶和椅子,糖逐渐从贵族的专属品,蜕变为平民的“解苦剂”。
以下是散落在典籍中与糖有关的时间列表,也是一张断断续续的甜味线路图,人们或可由此找到甜物质的源头。
西周:《诗经》关于糖的记载“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大意为周的土地异常肥美,连堇菜和苦菜也像饴糖一样甜。饴糖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硬糖。
东汉:《异物志》描述了作为主要产糖物质的甘蔗,“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日糖”。这便是红糖制作的“雏形”。
北魏:《齐民要术》记载了饴糖的做法,“取黍米一石,炊作黍,着盆中。蘖末一斗,搅和。一宿则得一斛五斗,煎成饴”。
唐朝:《新唐书》记录“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国,古代中印度之国)取熬糖法”,这是官方正史中的记录,明确中国最早的制糖术来自印度。
南宋:王灼《糖霜谱》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关于植蔗和制糖的科技专著。
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对砂糖的物理性状作了描述,“凝结如石,破之如沙”,并在“沙糖”条下记载:沙糖“和脾缓肝”“补血,活血,通淤以及排恶露”。沙糖,就是现在的红糖。
当代:1998年,季羡林完成七十余万字皇皇巨著《糖史》。
……
所有与糖有关的文字大概都是带甜味的。犹太人让孩子亲吻带有蜂蜜的书本,就是为了让他们记住书本是甜的,阅读是甜的。那些甜味就像是由最深沉的大山所酝酿的甜美溪流。人类为了获得它们,曾在春天的花田里寻找,在夏天的果园里寻找,直到找到那片甘蔗林。
2 就像春天发轫于一朵花,人类最清澈、最恰到好处的甜来自一株叫“甘蔗”的草本植物。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出征印度时,部下中曾有人告诉他此地出产一种无需蜜蜂就能产出蜜糖的苇草;当他结束对印度的征战返回时,也将这奇异的植物带回。从此,甘蔗跟随亚历山大的军队传入欧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珍贵的商品。
印度既是佛陀的故乡,也有可能是甘蔗的原产地。甘蔗大约在周宣王时传入中国南方,先秦以“柘”称之,到汉代才出现“蔗”字,它们的读音可能都来自梵文。季羡林先生的《糖史》可谓这方面的权威著作。
这种遍植在广袤大地上的禾本科植物,为多年生高大实心草木,天生就有“清热生津,润燥和中”之效,被医家列为“补益药”。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感觉世间万物皆有其时,世间万物皆有其用。
很小的时候,我就像蜂鸟那样对甜味着迷:吸食栀子花的花蜜,像嚼食甘蔗那样嚼食茅草根或玉米秆子以获得那一点点稀薄的甜味,吃完糖果后留着糖衣夹在书本里特意闻那淡淡的甜香……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某种难以言喻的欢乐。我还知道哪种植物叶片富含甜分,哪种果实汁液丰盈、鲜甜,哪处山岩壑谷里的泉水有股特别的清新、甜润之气。那时候,好像大地上长出的所有东西都是能吃的,都带着甜味。
中国甘蔗产区主要分布在北纬24度以南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而浙江台州黄岩头陀镇所在的北纬28.62度也有甘蔗种植。从宋朝开始,这个位于黄岩中部的小镇就开始栽种甘蔗了。而我生活的北纬29.09度的村落却没有甘蔗,我们种向日葵、油菜、小麦。我们总是把玉米秆子当甘蔗嚼——它们中也有甜的,淡淡的甜也是美味,也弥足珍贵。
卖甘蔗的小贩把摊位支在学校门口或戏台前,把长长的紫色的、绿色的甘蔗,斩成一小节、一小节。一毛钱一节。硬硬的外皮里装满甜汁。那时候,所有能吸引我们的食物都是甜的,水果糖、爆米花、柿子、柑橘,其中以甘蔗的甜最为清润和惊心动魄,就像大地深处涌出的甘泉。
P2-5
展开